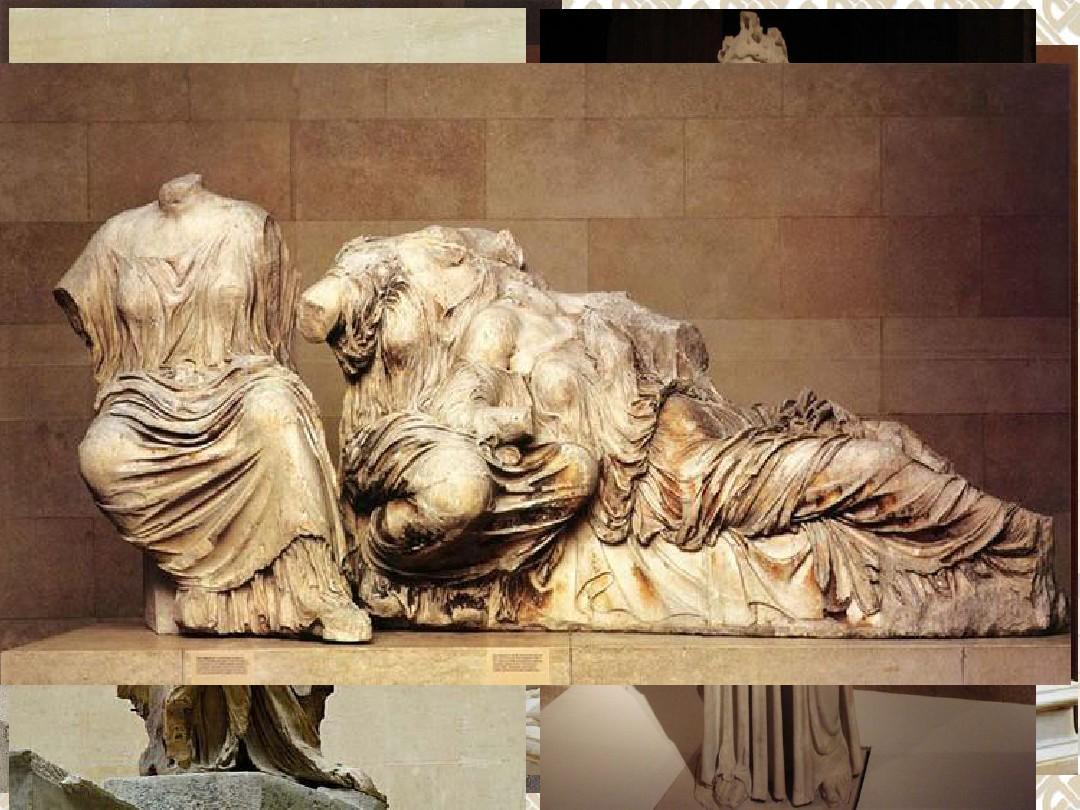程相占
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作为一个术语,正式出现在美国学者舒斯特曼发表于1999年的一篇论文中,这位学者又在2008年出版了专著《身体意识——凝视的哲学与身体美学》。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突出了副标题中的“身体美学”而将之译为《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身体美学由此引起了国内学者的较多关注。但综观国际学术界,真正以“身体美学”作为标题的专著并不多见,王晓华的新著《身体美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简称“王著”)是我所见的首部同类著作。
客观地说,王著的书名有点“文不对题”,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身体美学”—不是研究身体作为审美对象、身体作为审美主体、具身的审美活动等问题的著作,而是“回归身体”或“回到身体”的美学。作者特别强调的是,他要“在身体的基础上重建一切”,彻底地把美学界定为伊格尔顿所说的“有关身体的话语”(第19页)。作者甚至提出,美学就是“研究身体与世界审美关系的学问”(第一章第三节标题),美学就是“身体美学”(第36页)。这就意味着,王著所说的身体美学已经不是美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而是整个美学领域的全部—它与其他美学形态诸如艺术美学、环境美学、身体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等已经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涵盖关系。这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学术意图。
为了实现自己的学术雄心,王著首先对关键词“身体”进行了重新理解: 身体就是从头到脚的整个“全体”,也就是说,身体包括“头颅”。这个近乎常识的出发点推导出了王著所坚持的“身体一元论”:头颅是身体的一部分,头颅里面有大脑,大脑的功能是思维和意识,而思维和意识在哲学史上通常又被称为“心”或“心灵”,心灵的形而上层面则又被称为“精神”或“灵魂”。既然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心灵甚至灵魂也都顺理成章地是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以笛卡儿为代表的“身心二元论”只不过是在宗教神学影响下所产生的错误观念;根据生态学家海克尔的有机体一元论可知,只有“身体一元论”。因此,王著提出,通常所说的“我有一个身体”是不准确的表达,因为它一方面隐含着“我还有一个心灵”这句潜台词,另外一方面还隐含身体是由独立于身体的“先验主体”所“拥有”的;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我是身体”—除了身体之外,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是。“有”与“是”尽管是一字之差,但其隐含的哲学立场却天壤之别:前者是身心二元论,后者则是王著坚持的身体一元论。正是借助身体一元论,王著回答了“为什么美学必须回归身体”这个关键问题。
从进化论、生理学或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身体一元论或许很容易理解,但是,对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西方文化来说,公然否定灵魂存在的观念总会产生震动。因此,即使那些极其重视身体的西方哲学家诸如梅洛一庞蒂、舒斯特曼等,都在身心问题上模棱两可。而王著则断然宣称,宇宙间并不存在灵魂,只有身体一元论才能恰当地解释人的生命及其审美活动。这既是对于西方身体哲学的一个大胆突破,又是对西方灵魂形而上学的一次批判,其学术勇气颇为可嘉。
在提出并解释“为什么美学必须回归身体”这个问题之后,王著以身体主体论作为立足点,用五章篇幅依次讨论了审美的发生、审美的过程、审美的二重性、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等五个问题。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第五章对于自然审美的讨论。众所周知,自然审美(近似于通常说的“自然美”)问题是美学理论的难题,甚至是一种美学理论学术水准的“试金石”:衡量一个美学系统的理论价值及其成熟程度,首先应该看它能否适当地解释自然审美问题。王著从追溯身体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从审美史的角度审视了“轻视身体”与“低估自然”两个不同问题的内在关联,然后从论述“重身与体物”的关系入手,相当充分地论述了“自然审美的可能性”问题。其最精彩的地方是借鉴生态学思想,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 communism)理解为“共同体主义”(第218页)。“共同体”( community)又称“群落”,是生态学的关键词,美国学者利奥波德甚至将生态学称为“研究共同体的科学”。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看,共同体之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成员;人和其他物种之间的边界并不那么清晰,并非只有人才是主体,万物也都是主体;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哲学所说的“主体一客体”关系,而是“主体一主体”的关系,即“主体间性”关系。人以自己的身体构建自己的世界,万物也都以自己的身体构建各自的世界。比如,一朵花,也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生态学所说的“生境”< habitat)。对于花的欣赏,就不是传统审美理论所重视的欣赏花的优美形状、艳丽色彩、芬芳气味等,而是“进人花的世界”,“以花的身份去生活”;此时的花不再是物,“而是与我进行呼唤响应的主体”(第122页)。这些论述明显超越了传统的自然审美理论,特别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人化自然”理论,是对于当代生态审美思想的重要贡献。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作者长期的生态研究。身体美学与生态美学由此汇合在一起。
上文提到,王著的主体部分依次讨论了五个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这个问题清单当中,有哪些是作为“身体美学”的美学所提出的新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是已有的美学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追问就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问:为什么该书之前的“心灵美学”也能够提出这些问题?作者对此显然没有深究。其实,从当代美学前沿领域来说,环境美学已经对此问题有所探讨。环境审美不同于艺术审美的根本特点是,欣赏者只有走进并融人环境之中,才能对环境进行适当的审美欣赏;走进环境之中的显然不是人的“心灵”或“精神”,而是人的“身体”:实实在在的身体作为欣赏者的审美基点,通过相对于身体的不同方向(前后左右上下)、身体的高度或姿势(或直立、或弯曲、或坐、或躺等),根据欣赏者的审美兴趣,从包含着丰富信息的环境之中,选取引起审美关注的事物组建成审美对象,也就是动态地、随机地与环绕欣赏者的周围事物构成审美欣赏关系。正因为如此,环境美学也非常重视身体。这不正是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所引发的新的审美问题吗?我们不妨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来概括这个审美问题,比如说,“身体关联”( somatic relevance )。从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身体美学与环境美学相互贯通的学术契机。诚如是,王著试图以身体美学一统美学天下的学术雄心或许可以进一步尝试,其学术思路是,对于其他美学形态进行更加全面的把握与整合。
从论述方式的角度来说,笔者觉得王著也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王著的学术抱负是从身体一元论、身体主体性出发,对美学做出“原创性建构”(第26页),从而“由理论的学徒升格为创造者”(第43-44页),这是令人极其敬佩的学术魄力。但是,我们都知道,不要说“原创”,就是一般的“创造”,也必须以此前的美学史作为基础。如果对于美学史没有足够深刻的把握,除了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的天才之外,“原创”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创造”了出来了,在缺少美学史参照的情况下,其创造性也难以衡量和评价。我之所以很少提“美学创新”而长期坚持“审美理论知识有效增长”这种学术信念,原因就在这里。
根据这种学术信念,我对王著提出如下质疑:既然王著认定美学必须回归身体而成为“身体美学”,那么,它所隐含的理论前提就是此前的“心灵美学”无法恰当地解释审美现象,所以才需要改弦更张。那么,更有说服力的论述方式,就是根据“审美理论知识有效增长”这个原则,层层递进探讨如下五个个问题:心灵美学的思路是什么?其理论贡献是什么?其理论缺陷又是什么?身体美学为什么能够弥补这些缺陷?身体美学的独特审美问题又是什么?其中,第四、第五两个问题应该是学术研究的落脚点和独特贡献之所在。比如,康德美学可以说是西方心灵美学的典型代表,它建立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之上,从中基本上无法看到身体的影子。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王著不少地方却引用了康德美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就造成了一个疑问甚至悖论:作为心灵美学代表的康德美学,为什么能够支持王著这部身体美学著作?康德心灵美学的合理性来自哪里?身体美学又在何种意义上克服并超越了它的局限?
探讨这些问题无疑会大大增加王著的工作量,但无疑也会大大增强王著的说服力和理论厚度。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哲学就是哲学史;我们可以套用过来说:美学就是美学史。离开了对于美学经典的研读、反思和批判,美学研究必将成为空中楼阁,“原创”云云顶多是美好的学术愿望而已。有鉴于此,王著大量地追溯了西方美学史,但是,其学术针对性和批判力度都还有待加强。好在作者正处于学术创造的活跃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不久就会拿出更加厚重的学术力作。
源发刊物: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