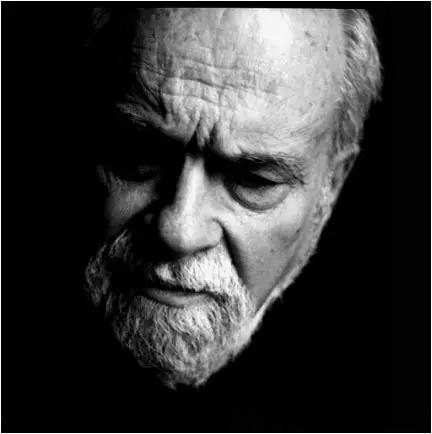高建平
当代中国,美学的复兴与危机并存。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需要有艺术和美学的提升,以对社会中的拜金主义趋向形成平衡、补充和救赎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家和政府的倡导,社会舆论营造的大气氛,以及艺术升科等各种手段,使艺术和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得到了补充和优化。这些都对美学在当代的复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之后,在90年代出现了美学的冷却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美学正在中国复苏。最近一二十年来在中国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以及国外美学著作和翻译、介绍,学术交流,对美学的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美学并非由此走上了康庄大道。实际上,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危机四伏。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美学的危机首先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学术圈里被人们从思辨哲学的方面来理解。美学与思辨哲学具有同源关系,这个学科从其一开始起,就与思辨传统的哲学联系在一起。例如,鲍姆加登将美学看成是低级认识论,康德将美学看成是理性作用于感性的判断,黑格尔将美学看成是理性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美学学科经典作者的意图,当然都是正面的,是想创立和发展这个学科。但他们所能做的事,只不过是在理性得到高扬的时代,通过思辨的论证为美学保存一席位置。这一传统是美学这个学科所赖以成立的依据,也恰恰成为这个学科在当代失去吸引力的原因。美学知识需要面向大众,面向生活,而向艺术家,但这个学科的思辨传统却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现代学术在性质上经历了一个从规训向分享的转化。所生产出来的思想和知识,如果本身没有吸引力,就难以赢得大众。康德、黑格尔的时代过去了,不能再用那种方式生产美学的知识。这是在当代美学知识难以获得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其实,老一代学者就曾经意识到这一点,在美学知识大众化方面作过许多尝试。这方面的矛盾到了今天变得更加突出了。
第二个方面,一些当代中国美学家们对上世纪50年代的探索和80年代的辉煌感到荣耀,潜心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从而进行阐释。这种研究如果是以学案分析的方式,澄清史实,说明原委,清理线索,那当然是有价值的。历史需要积累,不能在不断追逐学术时尚的同时不断遗忘过去。有时,过去的知识中也能找到新知识的生长点。但是,如果钻进当时美学几大派的争论之中,寻求成为其中某一派在新时代的传人或卫士,重复当年的争论,为某一派寻求排它性的位置,这就失去了意义。这样做的效果,只能是复制过去的争论,不问当下的现实,不接触文学艺术,把原本在特定理论语境中生长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思考变成干巴巴的教条。至于一些人不惜歪曲史实,以便证明自己师尊的伟大和对手的渺小,从而捍卫自己学术师承正统性,就更没有什么价值。这种学术倾向,对当代美学的复兴构成了干扰,以学术的名义,达到反学术的效果。
一个学科要复兴,有待于这个学科符合社会的需要,更有待于社会对这个学科倾注热情。我们这个社会对美学的热情耗尽了吗?新的热情从何处生长出来?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继续对美学的对象方法作古老的,经院式的规定,已经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也不利于这个学科的发展。
我们看到,对环境和生态的热情向美学的延展,对乡村改造和城市发展的热情所引发的美学思考,对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热情与美学的结合,当然,更为密切的,是与艺术学科的联系。
在当代中国,艺术面临着种种发展的机遇。经济发展带来的艺术需求,中国艺术在国际艺术界和艺术市场上的成功及其在国内的衍生影响,艺术升科所带来的体制上的支持,都推动着艺术研究的繁荣。这种艺术发展的机遇,本应是美学发展的机遇。然而,出于种种实际的考虑,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学的艺术学科被创造出来。一些学者努力在进行一些切割,宣称他们在研究一种学问,叫做艺术学。这种艺术学与美学无关,或者是反美学的。对那些实际的考虑,我们无法掌控,是位置决定思维,或者用粗俗一点的话说,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有人将之看成是真理,那当然不值一驳,不过是属于混迹于行政部门的无脑人的自我解嘲而已,当不得真的。然而,艺术学和美学之间,确实有着一些不同的指向,或者不同的侧重。当这种差异被夸大以后,就出现了艺术研究中的反美学倾向。
在当代先锋艺术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出现了一种对审美追求的超越。过去,艺术追求美:高雅的艺术,就是美的艺术。以美为目的叫创作,是艺术;不以美为目的叫制作,是工艺。对美的理解,后来也逐渐宽乏。艺术作品不一定只写反映美的事物,也反映丑的,美丑对照的事物。有人提出,艺术不是只是提供“美”,也要提供“表现”,只有真情,人的各种感受都可凝聚成艺术。有人提出,艺术是“表现”与“再现”的结合,既表现内在的真情,也再现生活的真实。还有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中积淀着情感。如此等等。形形式式的艺术理论挑战了传统的“美在形式”和“艺术是摹仿”的观点,从而出现了理论的空前繁荣。
然而,这些理论都在一些先锋艺术的面前却碰了壁。此前种种艺术理论,尽管否定艺术与美的关系,但它们只不过是将美的概念扩大,从而将崇高、丑、幽默搞笑,以至奇特、荒诞、怪异,以及其他种种能引起人情感反应的对象包括在内。这时,艺术尽管不再展现或创造美,但毕竟仍与人的某种审美的,或感性的反应有关。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先锋艺术所带来的挑战是,一些被认定是艺术品的物体完全不与其所激起的感性反应联系在一起。例如,有人说杜尚的《泉》是艺术品,是由于杜尚在寻常物中发现了过去没有发现的美。这种解释显然是可笑的,《泉》被认定为艺术品,与它的光泽和造型无关,这只是艺术史上的一个事件。与此相应,展示几个语词,或者某个现成物、拾得物,并宣称这些是艺术品时,也与光泽与造型等外在感性特征无关。这样一来,当艺术不再以其所激起的感性反应而被认定为艺术时,这种艺术也就与美彻底断绝了关系。艺术与美不是一回事,与感性反应不是一回事,因此艺术学也与研究美与美感,被说成是“感性学”的美学无关。
更对美学这个学科具有杀伤力的,是艺术内部的反美学倾向。艺术研究不能等同于美学研究,它的范围与美学并不重合。艺术史研究,艺术考古,艺术作品评论,艺术的技法研究,等等,都与美学无关。艺术学科成熟的标志,是该学科所涉及到的各个学科分支齐全,研究分工有序,并各自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但是,许多艺术研究者将这些研究与美学研究对立起来。他们将艺术的研究,等同于一种对“物”的研究,认为艺术是“物”,只有对物的研究,才能避免将研究导向空洞无物。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分野:美学研究精神性的对象,艺术学研究物质性的对象。精神性的对象不可捉摸,而物质性的对象就在眼前。精神性的探讨趋向于空谈,物质性探讨趋向于行动。如此推导,要艺术学,不要美学,成了当然的要求。
美学过去曾经是,而且今天仍然是艺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术界喜欢重复黑格尔的一段话,认为美学的正确名称,应该是“艺术哲学”。这句话在很多人那里,也曾被解读成对美学的消解,或者说是用“艺术学”来取代“美学”。实际上,正好相反,黑格尔要做的事,恰恰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统摄艺术研究,从而在艺术研究中注入一种精神性。
前面曾提到思辨哲学的终结,但终结之后的思辨哲学,仍以新的形态保持活力。在经过重新解读以后,黑格尔在20世纪哲学中,渗透到许多重要的艺术哲学研究流派之中。例如,一位重视科学,长期跟踪科学最新发展的哲学家和美学家约翰·杜威,恰恰是由于黑格尔的拯救,才没有滑向唯科学主义;一位关注艺术的物质性,对具体的艺术作品感兴趣,热衷于分析哲学的阿瑟·丹托,也正是由于黑格尔的影响,才保持了对艺术发展历史的宏大的视野。黑格尔将不同历史时期艺术特点,不同的艺术门类所呈现的特点,编入到一个宏大的精神史的序列中,看到一个超越具体艺术风格和门类,超越具体工具和技术的进步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独特“艺术终结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在今天仍起着一种理论的救赎的作用。
对于艺术研究来说,今天的美学所起的作用,恰恰与此相接近。美学以其对精神性的追求,以其批判精神,将艺术研究从对“物”的追求,从技术与掌故之学中解救出来,使之看到历史的延续性,看到一种精神性的作用。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那种艺术与美的分离的观点,固然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举例说明,但毕竟不能代表一个总的趋势。与美分离,不再追求美,或者说,不再追求感性反应的艺术,是一种即将终结的艺术。但周而复始,终结后还会有新的开端。艺术与美还会相互吸引,在新的进代,新的艺术语境中,美学还会作为一种营养,被艺术研究所吸收,从而在艺术学中获得新生。
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艺术学不是,也不应该是美学的终结,而是美学的新的拓展。
[原载《上海评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