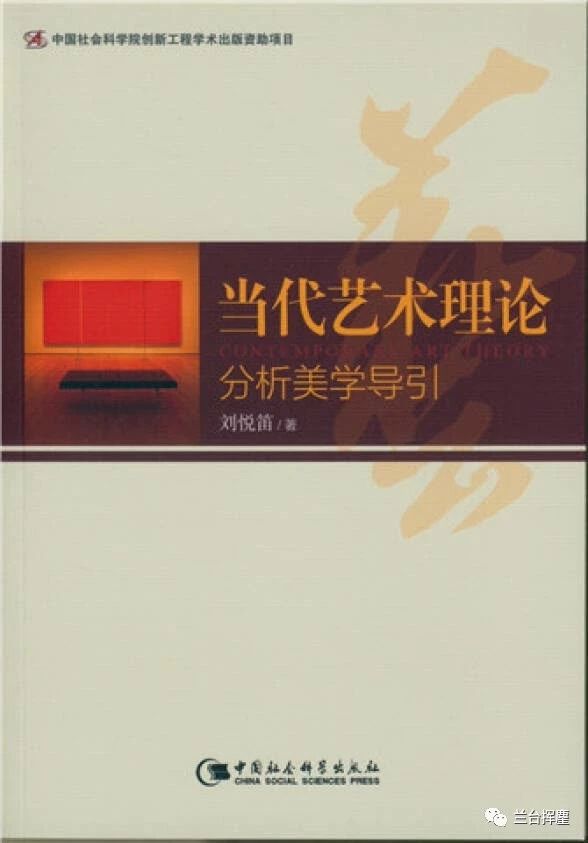刘悦笛
“艺术学”是来自德国的概念,在英语为主导的国家如英美并没有艺术学的建制,中国艺术学的建构曾深受德意志的影响。[1]但是,目前在以英文为主导的全球学界,对“元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主要就是由“分析美学”(Analysis Aesthetics)做出的,分析美学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占据唯一主导的艺术哲学思潮。“分析美学”致力于对于一切艺术进行哲学化的研究,这样就既面对了所有艺术门类,也将艺术学研究上升到“元”的层面,亦即最基本的理论层面。 [2]所以,在英语为主的欧美学界,分析美学研究对于“元艺术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本文就以“分析美学”研究来主,来探讨“元艺术学”的理论架构。
在笔者新著《当代艺术理论:分析美学导引》当中,笔者深描了当代艺术理论的十个基本问题,试图建构一套“元艺术学”的基本理论架构。[3]这十个艺术理论的基本问题,皆为欧美的“分析美学”的核心成果。作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唯一占主流的美学思潮,从维特根斯坦至今,门罗·比尔兹利、理查德·沃尔海姆、纳尔逊·古德曼、弗兰克·西柏利、约瑟夫·马戈利斯、阿瑟·丹托、乔治·迪基、斯蒂芬·戴维斯、杰罗尔德·列文森和诺埃尔·卡罗尔,一代又一代代分析美学家围绕这些基本问题寻思作答,其中,沃尔海姆的“视觉观看理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迪基的“艺术惯例论”和戴维斯的“音乐表现论”,无论在艺术理论界还是艺术实践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艺术理论:分析美学导引》的每章都采取了这样的结构,引子是从艺术家个案的解析出发,然后逐步引入理论的深处,最后做出整体述评进行总结与反思。每章皆以“元艺术学”的述评为反思起点,我们特别强调的是本土的独特视角,并力求建构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艺术原论。
一、艺术本质观:艺术到底是什么?
艺术本质观(Nature of Art),从杜尚的“自行车轮”谈起,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艺术是“开放概念”;2. 从“艺术界”框定艺术;3. “惯例性”艺术定义;4. “历史性”艺术定义;5.艺术作为“丛概念”。
在当今时代,追寻“艺术本质”,从而确证“艺术定义”,应该说,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目的。我们认为,这种两个目的是基本合一的,都是为了“确定艺术”(indentifying art)。这是由于,艺术从“现代主义”开始,就进入到了激进变革的时代,尽管在前卫冲动日渐消耗之后,当今的艺术动力正在逐渐衰落。所以,艺术哲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当代艺术的激进变化,其核心问题就是“发现确定的方法”,以确定哪些对象能为艺术,这个任务在“先锋派”时期就曾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4]这也就是说,即使你不承认艺术存在本质,不认为艺术可以定义,但是“确认艺术”的基本方法还是存在的。我们打个比喻,界定艺术的传统方式,就好似是去确定“什么是雪山”?以往的艺术定义,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地确定之。从传统的“再现论”到“表现说”,从“形式论”(“有意味的形式”论)与“直觉说”(“艺术即直觉”论),从情感说(“情感的交流”说)到符号学(“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论),都是说雪山之为雪山,乃是由于上面下了雪并积了雪,无论是情感、直觉、形式、符号都是对雪的规定,这种界定方式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过时了。
如今的艺术界定方式,同样以定义雪山为例,乃是要寻求雪线在哪里?这其实是一种分析式的界定,就是要确定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在划定了这个边界之后,才能确定哪些归入艺术,哪些属于非艺术疆域。以“惯例性”定义的巨大影响为例,当艺术学家寻求使得某物成为艺术的“习俗”的时候,也就是在寻求艺术与非艺术的的区分到底在哪里。“惯例性”艺术定义包含了当今艺术定义的四个层面:其一,Who的问题:“谁”来确定某物被欣赏的候选地位?当然是艺术界的核心人物,首要地代表了艺术世界的社会惯例。其二,What的问题:具有哪些特征的对象必定成为艺术品?原则上说,一切对象都可以成为被欣赏的对象。其三,How Much问题:理论家们总是松动惯例论的程度以纳入更多艺术在其内。其四,How Many问题:究竟存在多少个艺术世界?[5]无论艺术界到底有多少,它们都是不断变动的,同样,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都需要确定——“何为艺术”。
二、非西方定义:艺术何以非西方?
非西方定义(Non-western definition),从非洲土著造物头饰谈起,主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原始艺术是艺术吗?2.艺术与非艺术之分;3.功能与非功能之间;4.文化与跨文化之际。
当代西方美学对于“艺术定义”的主要贡献,是由上世纪后期主导的分析美学做出的。然而,随着东西方互动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分析美学的内部,出现了非西方化的定义新趋势,这使得探讨一种全球艺术定义成为了可能。当今西方艺术理论也都开始将非西方的视角纳入其中,并重在追问“何为艺术”的非西方观念,由此来看艺术究竟是由情境决定还是文化决定的,到底是有生物根基的还是有普遍基础的[6]。但无论答案如何,在考虑全球艺术理论之时,非西方的艺术观念都必须被整合在其中,这已成为了推动艺术的全球性界定的基本动力之一。
有趣的是,尽管分析美学家们一股脑地将所有的原始艺术都纳入“艺术体系”,但是,某些人类学家们,特别是艺术人类学家与审美人类学家们却提出了相反的主张——根本不存在非西方艺术,艺术只是一个西方的概念。甚至在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当代人类学研究在面对艺术问题的时候,开始用“生产者”取代“艺术家”的概念,用“视觉形象”的概念取代了“艺术的”概念。[7]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欧洲人最早将黑非洲的原始部落的物品纳入到自身的艺术体系之后,非西方文化的人工制品才被认定为了艺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欧洲人将人类学博物馆里面的东西搬到美术馆、博物馆当做艺术品的浪潮即为明证。在做出此类的判断之后,也就是认定艺术就是西方的而不是非西方的之后,一般就会有两种继续做出判断的可能:一个是非西方文化里面没有艺术概念,也没有与西方相对应的艺术概念;另一个则是非西方文化里面尽管没有艺术概念,但是却有着与西方艺术概念相对应的独特的本土概念。 “非西方艺术定义”正在全球拓展当中。
三、艺术本体论:艺术品如何存在?
艺术本体论(Ontology of Art),从伦勃朗原作还原为赝品谈起,主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艺术是“单一”还是“复合”的?2.艺术是“自来”还是“他来”的?3.“记谱”与“非记谱”两个艺术系统;4.作为“类型”与“殊例”的艺术。
在分析美学视野当中,艺术是如何存在的哲学追问,主要聚焦于艺术“作品”的存在的哲学问题,而毫无疑问,作品作为绝大多数的艺术活动之产物而存在的。这种研究是对艺术品究竟是如何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哲学追问。本体论的追问在20世纪后半叶也是占据主流的,“艺术本体论”与“艺术本质论”一道成为了分析美学居于核心地位的难题,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分析美学家们的持续追问。实际上,“艺术本体”的探讨将反过来深化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
随着分析美学的更为深入的发展,对于艺术本体论的研究,如今朝着为更为深入的方向加以拓展。在由此形成的“多元化”的视角看来,艺术品“是’公共的’而且是’可知觉的’……;它们拥有‘客观化’的属性,但这些属性有些是本质性的有些则不是;它们是‘文化对象’,依赖于文化条件的融入与持续;它们基本上是与‘人类活动与态度’相系的实体;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如被艺术家所创造;它们‘成为存在’并‘不再存在’……;它们的身份条件是被价值所标识的,这就区分于自然界当中以功能来定义的人造之物或者物理对象。”[8]当今的分析美学家们,恰恰就是按照这些思路来进行探索的,这种对于艺术品存在状态的深入研讨,无疑为艺术到底如何存在的难题进行了全方位拓展,诸如“文化论”角度、“活动论”角度与“价值论”角度都成为了研究艺术本体论的新方向。自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分析美学所进行的艺术本体论探讨,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艺术自身作为对象,而忽略了非西方传统作为“他者”的存在。按照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去追问艺术究竟如何存在的问题,就难以建构起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艺术本体论。
四、艺术形态学:艺术品因何分类?
艺术形态学(Art Morphology),从库奈里斯的“总体”艺术谈起,主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 艺术作为“个体化殊例”;2.艺术作为“活动的类型”;3.艺术作为“活动的对象”;4. 艺术作为“施行的活动”;5. “大众艺术”本体论;七 “混合类型”艺术本体论。
艺术品是以何种形态存在于世的?不同艺术形态的特征是什么?某种艺术形态与其他形态之间如何区分?这就是“艺术形态学”的问题,从“活动论”的艺术本体论,再到“大众艺术”与“混合类型”研究,都已经进入到形态学的领域。传统的艺术类型学认为,艺术是可以按照时空进行分类的。从历史上追溯,按照《拉奥孔》的解释,如果说,诗是时间艺术,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相续的话,那么,绘画则是空间艺术,用空间当中的形和色加以组构。在近代西方文化当中,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被严格开来,音乐是最典型的时间艺术,而绘画则是最典型的空间艺术,德文Raumkunst这个词就特指以造型为主的空间化艺术。然而,这种时空观只是牛顿意义上的固定时间观,从狭义到广义的相对论对此进行了颠覆,当代艺术更在质疑这种时空不变与分离。
直到现代和后现代以来,艺术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愈来愈走向了开放。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在于:对“美的艺术”边界的突围。在现代主义艺术中,“非美”的艺术被大量地纳入到艺术界域内,如远离古典美学规范的丑的艺术、荒诞派的荒诞艺术、达达主义的“艺术化的反艺术运动”[9],如此等等。在后现代主义艺术里面,博伊斯和安迪·沃霍尔们消抹艺术边界并延伸艺术概念,将原本的“非艺术品”当作艺术来理解,从而又擎起了“反艺术”的旗帜。同时,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原本被划出“美的艺术”之外的设计和建筑,也逐渐回归到艺术的阵营,更不用说影视艺术的出现所造成的视觉文化转向了。尽管而今所谓“非艺术”与“反艺术”都退出了流行阵营,“对艺术界人士而言,下述事实已经非常明显:反艺术的攻击性被驯服,非艺术的否定性也被否定、升华或演变为肯定性”。[10]但事实的确是,艺术正在走入了一个“开放的时代”,当今元艺术学由此对于艺术进行了崭新的类分。
五、艺术经验观:审美与艺术相关吗?
艺术经验观(Art experience),从库苏斯以观念反审美谈起,主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从古典到当代的“审美转型”;2.审美与判断的“二律背反”;3.艺术的“审美定义”理论;4.审美与非审美之争辩。
自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艺术与审美之间开始建构了稳固的联系。如果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艺术与审美的关联,其实也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现代性建制”。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性产生之前,艺术与审美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历史关联,随着现代性的建构,二者之间形成了交互规定的关系,但是从现代主义直到后现代艺术运动,艺术与审美逐渐脱离了关系。但必须承认,全球社会并不都转入到“后现代社会”,即使高度后现代文化里面,也还存有现代乃至前现代性的艺术要素。所以,审美与艺术之间的关联仍是复杂的,审美、非审美与反审美之间形成了网状关联,这恰恰也是“后现代性”的特质所在。
当强调艺术与审美的结合的时候,就形成了“艺术自律论”,而当二者分立当时候,“艺术他律论”则渐渐居主流。其次,无论是极端的“自律论”还是僵硬的“他律论”,其实都具有某种合理性,都把握到了真理的一面。换而言之,“自律”与“他律”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是最抽象的绘画、最注重音韵本身美感的无调音乐、最关注语词排列的先锋诗歌,都是在某一历史语境里面产生出来的,而根本不可能成为超时空的存在。同理可证,即使是那些要求为某种政治力量直接服务、为某种社会组织所利用的艺术形式,也必然遵循艺术的规律进行创造,而不能简单地成为“时代的传声筒”。如此看来,“自律论”与“他律论”恰恰站到了“艺术掌握”的两极上,它们也无疑是两种“艺术掌握”的不同形式而已,缺一不可。然而,自律与他律毕竟都是来自西方的范畴,仅仅强调“自律论”与“他律论”执其两端还是不够的,更关键的是,如何使得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在自律与他律之间形成一种交互性的融合。
六、审美经验论:审美经验由何确定?
审美经验论(Aesthetic experience),从培根的肖像三联画谈起,主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为审美经验辩护”;2. “审美经验的神话” ;3. “审美经验的终结” ;4. “审美经验的复兴”
作为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占据主流的美学流派,分析美学除了始终聚焦于“艺术”这个核心问题之外,还对于“审美”问题研究继续加以推进。在“艺术”与“审美”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前一方面的核心问题无疑就是“艺术定义”,而后一方面的核心问题则是“审美经验”的问题。在倾向于”新实用主义”传统的美学家看来,而今美学的主题已经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转向了以“经验概念”为中心,对“艺术对象”的考察业已转向了对于“经验特性”的探讨。[11]尽管这种描述囿于分析美学的视界确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道出了“审美经验”研究后来者居上的发展走势,但这种复兴并不是全局性的,更多显示出来的只是某种复兴的症候。
与给艺术下定义的历程一样(从传统的艺术定义方式到“艺术不可定义”再到给艺术下一个相对周全的“定义”),对于“审美经验”的探讨,也经历了——从传统的审美观念转向对于审美的“消解”再到积极的审美“建构”——的诸多阶段。但与界定艺术不同的是,分析美学的审美经验观在20世纪后半叶中段主要是被批判的对象,“消解审美”曾一度形成了主流,但这种趋势逐步得到了遏止,“审美复兴”逐渐成为了某种共识,言过其实者更喜欢称之为“审美经验的转向”。这种对审美状态的关注包括如下层面:“1. 对于心灵的审美状态区分于其他心灵状态的思考,在某种方面,这种状态类似于感性愉悦或者麻醉剂诱发的经验,这种状态也是区分于与人类关注的其他领域相关的诸如宗教、认识、实践和道德之领域;2. 对于既不诉诸于任何审美的先验理念也不诉诸于艺术概念的方式的思考;3. 解释特定审美的相关的理念,举例来说,依据心灵的审美状态的特定理念,去解释审美对象、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之审美特性、品质、层面或者概念;4. 多多少少地去为审美领域与艺术领域之关联做出辩护,尽管意识到了心灵的审美状态或许也是适当地直接指向或者建基于非艺术(例如自然)当中的。”[12]
七、艺术再现观:艺术如何去再现?
艺术再现观(Art representation),从皮格马利翁的雕刻谈起,主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解析再现论的传统 ;2.反错觉说与相似论;3.维特根斯坦的启示;4. “再现性的观看”;5.“视觉的双重性”;6.作为“假装”的再现;7.“再现”与“再现为”;8.“新再现主义”理论。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Representation”来自于古拉丁词“repraesentare”,现代法语相对都词也是同一词源,re-基本意为“再次”,praesentare则有“呈现”之义,合起来该词都直接语义就是“再次呈现”抑或“再度呈现”。[13]在源始性的意义上,“再现”本是就艺术与世界的基本关系而言的,这是一种广义的界定。这就是说,广义的艺术“再现”,并不等同于来源于“摹仿”意义的“再现”,并不是与(后来才出现的)“表现”相对意义上的狭义“再现”。如此看来,“再现”就包孕了双重的意蕴:其一,是来自摹仿抑或复制意义上的狭义“再现”;其二,用以言说艺术与世界的基本关系,这种广义的“再现”,既涵摄了一般意义上的“再现”,也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呈现”,它所表述的是艺术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问题。
元艺术学所谈论的狭义“再现”,可以具体到以“图像再现”(pictorial representation)为主,来论述再现的基本问题,分析美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从沃尔海姆的“视觉的双重性”理论,沃尔顿的“假装”再现理论,古德曼的“再现为”理论,再到丹托的“新再现主义”理论,艺术再现观在视觉领域得以层层推进。当然,在文学当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再现现象,特别是叙事性文学作品里面的“虚构”(fiction)问题,早就为分析美学家们所重视。一般而言,从再现的分析美学角度看,文学的再现聚焦于“虚构”,与之几乎相对,视觉抑或图像的再现则聚焦于“描绘”(depiction)[14]。正如音乐更与“表现”直接相系一样,“音乐表现”也是个常用词,图像也更与再现直接相关,“音乐表现”与“图像再现”也恰恰构成了当今元艺术学的两个聚焦点。
八、艺术表现论:艺术如何来表现?
艺术表现论(Art expression),从罗斯科的“色块”音乐谈起,主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解析传统的“表现论” ;2. “表现性”的更新换代 ;3.表现作为“隐喻例示”;4.多维“意义”的表现;5. “情感”的复合表现。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表现”,也成为人们理解艺术的基本方式之一。从西方创生到东方舶来,“再现”与“表现”又被直接对应了起来,似乎前者是面对外在世界,后者则是面对内在世界。然而,如果广义地理解“再现”,那么就可以说,“表现”也是一种广义的“再现”,是对于内在世界状态的一种呈现而已。一般的理解是,表现往往是与艺术家的情感相联,“表现与感受或情感的诉求和描述之间的基本差异,在18世纪就已成为了共识”,[15]实际上,艺术所表现的恰起是人们的内在生活世界。在传统意义上,所谓“表现理论”的确是与艺术家创作艺术品时的“艺术家经验”是直接内在相关的。
如此说来,反思一下我们对艺术所作出的反应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反应取决于两个相互联系的假定:“第一个假定是,艺术家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表现他们的感情;第二个假定是,这种表现是审美价值的源泉之一。”[16]当然,这又包含了价值论的理解,但事实上,表现不仅仅是“通过艺术家所实施的某一过程”,而且也是指“这一过程所产生出来的特征”,[17]表现理应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如果给予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再现与表现以更为现代的语言哲学之阐释,根据某种语言唯名论的理解,“再现”也不过是给了所应对的外物某种命名而已。按照这种思路,再现就是有名字的,而表现则是无名字的。因为,当人们给某物命名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再现某物”;然而,表现却“空其所指”,或者说指向了人类某种内在的状态。当然,在美学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分析美学的意义上,表现具有更为多元化的内涵与外延,多维“意义”的表现与 “情感”的复合表现皆被阐发出来。
九、艺术批评观:艺术以何做评价?
艺术批评观(Art criticism),从布尔乔亚的大蜘蛛谈起,主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艺术评价”的诸多类别;2.“艺术批评”的诸多种类;3.工具论的“认知主义”;4.“多元主义”与“一元论”。
如何评价艺术?艺术品如何被评价?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如何去“主观地”评价艺术?从客体的角度来说,艺术品如何被“客观地”得以评价?当然,主体的评价看似是主观的,但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联,仍使艺术评价的客观性问题变得愈来愈重要。这是由于,当一件艺术品被创造出来后,被置于艺术界当中,就要面临艺术评价的客观性问题,人们也要追问,这种艺术评价的普遍规则到底是什么?从艺术评价可以直接导向艺术批评的问题。这是因为,“评价就是批评的首要问题”,[18]无论怎样区分批评的内部种类抑或类型,评价都是批评当中的最关键的要素,批评显然是个更广的概念。那么,艺术批评的本质是什么?艺术批评的功能是什么?艺术批评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早就被分析美学所追问,甚至在当代艺术理论中被推到了高峰。
在20世纪的50、60年代,美学曾经一度被等同于所谓的“元批评”(meta-criticism),这在比尔兹利1958年那本名著《美学:批评哲学中的问题》当中得以集中论证。尽管在比尔兹利那里元批评几乎等同于美学的全部,但更公正地看,批评问题恰恰成为了分析美学的重要问题。这就引出了一门崭新的学科,也就是“批评的哲学”,元批评也应该是批评的哲学的一种独特形态。然而,与文学的“新批评”一道,元批评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衰微。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分析美学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也就是从其后点70年代开始,美学家们集中追问“艺术的定义”。与此同时,丹托这样重要哲学家与美学家,不仅关注艺术界定问题,同时也关注到来艺术批评的基本问题。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批评的哲学已经在美学当中获得了一席之地。[19]到了2009年,当代分析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以一本名为《论批评》的小册子,重提了批评的哲学在整个当今艺术学中的核心地位。
十、艺术价值论:艺术价值在何处?
艺术价值论(Values of art),从昆斯艺术商业帝国谈起,主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1.“艺术价值”的诸多类型;2.活动论的“工具主义”;3.审美的“非实在主义”;4.价值观的“普遍主义”。
在分析美学问题域的核心部位,艺术中的评价与价值的“客观性”问题无疑占有重要位置,并且它们也是内在关联的。由此,这就形成了分析美学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问题,即“艺术评价”与“艺术价值”。这两个问题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更多与“艺术批评”是相关的,批评家所从事的活动可以被当作是“说服”,批评家“所做的并不是传达信息,而是努力修正,或者说改变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态度”,这当然就需要对艺术做出评价。[20]后者则往往是与美学的“形而上学”是相系的,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是更高层的。“艺术价值”无需谁去说服谁,因为它本身就可以还原为某种固有的“态度”,而且,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当中所形成的,进而在某种特定的态度基础上确立并构成了某种“价值系统”,不同的价值及其系统之间又共同建构成美学上的“人类价值体系”。
“艺术价值”这个核心问题所追问的主要是,那些贡献出“价值”的艺术品的属性,如何才能从对于艺术品的鉴赏与接受当中得以生发出来呢?当人们对于某件艺术品做出判断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判断是如何能被批评抑或维护的?在确证了艺术价值或者审美价值的独立性之后,分析美学的哲学追问,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形而上的领域。当分析美学家们追问,一切艺术品都存在价值吗?这种价值就是“艺术之成为艺术”的形而上价值。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说明这位美学家一定持有相对主义的视角,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证明他走的是绝对主义之路。与此同时,除了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争,还有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之辩。当美学家确证价值判断始终是历史性的,他就是属于前者,如果他追寻的是本真性的普遍价值,他无疑就更倾向于后者。
十一、“元艺术学”系统:五层级基础架构
在逐层描述过“元艺术学”的十个基本问题后,我们再来考察“元艺术学”这十个基本问题,有可能形成何种理论架构与系统?
从结构上说,“艺术本质观”是第一层级的问题,“非西方定义”则是东方的相应解答方式,回答的都是“艺术是什么”的亘古难题,东西方的解答是相对而出的。“艺术本体论”与“艺术形态学”则是第二层级的问题,回答的是艺术品是如何存在与类分的问题,后者是前者的延伸,这些问题与“艺术本质”追问是相互深化的。“艺术再现”与“艺术表现”则是第三层级的问题,回答的是艺术呈现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问题,看似并置但其实前者较之后者有更深广的内涵。“艺术经验”与“审美经验”则是第四层级的问题,回答的是艺术经验与审美属性如何确定的问题,二者曾内在相关与交互规定,但又在彼此脱钩。“艺术批评”与“艺术价值”是后一个层级的问题,回答的是艺术如何评价与艺术价值何在的问题,评价问题会直接导向价值的追问。
由此可见,“元艺术学”理论架构的五个层级,就得以大致搭建而成: 
尽管《当代艺术理论:分析美学导引》试图给出一整套分析美学与艺术哲学的导论,或者说,力图为当代艺术提供一套“叙事模式”抑或一套“言说方式”,但所做的只是某种基础性工作而已。实际上,分析美学家们所建构的当代艺术理论,并不是座金碧辉煌的教堂,而是块充满脚手架的工地,后来者在前人的基石之上可以继续劳作。
质言之,一方面,从理论“审”当代艺术,另一方面,从艺术“思”当代理论,恰恰构成了《当代艺术理论:分析美学导引》的基本任务。所以,当我们言说当代艺术理论的时候,它就不仅是“当代艺术”的理论,而且是“当代的”艺术理论。
艺术理论,需要“当代”的更新;当代艺术,需要“理论”的升华。我们的艺术理论,滞后于艺术践行,缺乏“当代性”;我们的当代艺术,超前于艺术理论,亟待“匹配性”。当代艺术理论“在中国”要建构发展,就需要借鉴欧美学界最新的艺术理论,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代中国需要“中国性”的艺术理论,就需要把自本生根地生发出自创思想,所谓自我之根,可以生长。这也是《当代艺术理论:分析美学导引》出场的基本目的之一。
参考文献:
[1]刘悦笛:《从艺术学的“中国化”到中国化的“艺术学”》,《艺术百家》2013年第4期。
[2]刘悦笛:《分析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94-97页。
[3]刘悦笛:《当代艺术理论:分析美学导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4]Noël Carroll, Beyond Aesthetics: 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4.
[5]Howard S. Becker, Art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150-162.
[6]Kathleen Desmond, Ideas about Art, Chichester, West Sussex, Malden, M. A.: Wiley-Blackwell, 2011, pp. 15-32.
[7]乔治·马尔库斯、弗雷德·迈尔斯:《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梁永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Peter Lamarque, Work and Object: Explorations in the Metaphysics of 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0-61.
[9]沃纳·霍夫曼:《现代艺术的激变》,薛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10] 蒂埃里·德·弗迪:《“非艺术”的发明:历史》,杜可柯译,《艺术论坛》2014年第2期。
[11]Michael H. Mitias ed., Possibility of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ress, 1986, p.92.
[12]Gary Iseminger,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Jerrold Levinson, ed.,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 p. 107.
[13]David Summers, “Representation”, in Robert S. Nelson and Richard Schiff eds., 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4]Robert Stecker, Aesth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 An Introduc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pp. 163-200.
[15]Richard Wollheim, On Art and the Mind: Essays and Lectu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85.
[16]安妮·谢波德:《美学:艺术哲学引论》,艾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7]John Hospers, “Problem of Aesthetics”, in Paul Edward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and The Fres Press, 1967, p. 46.
[18]Noël Carroll, On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9.
[19]Noël Carroll, On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1.
[20]安妮·谢泼德:《美学:艺术哲学引论》,艾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原文发表于《艺术百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