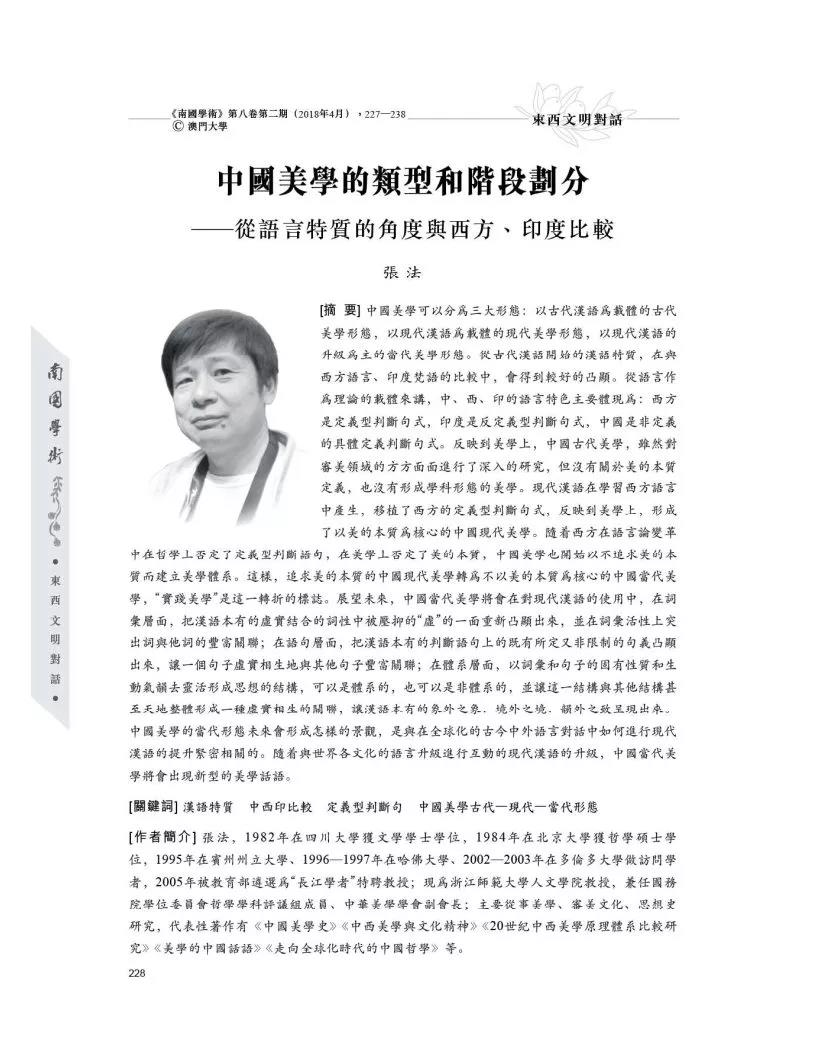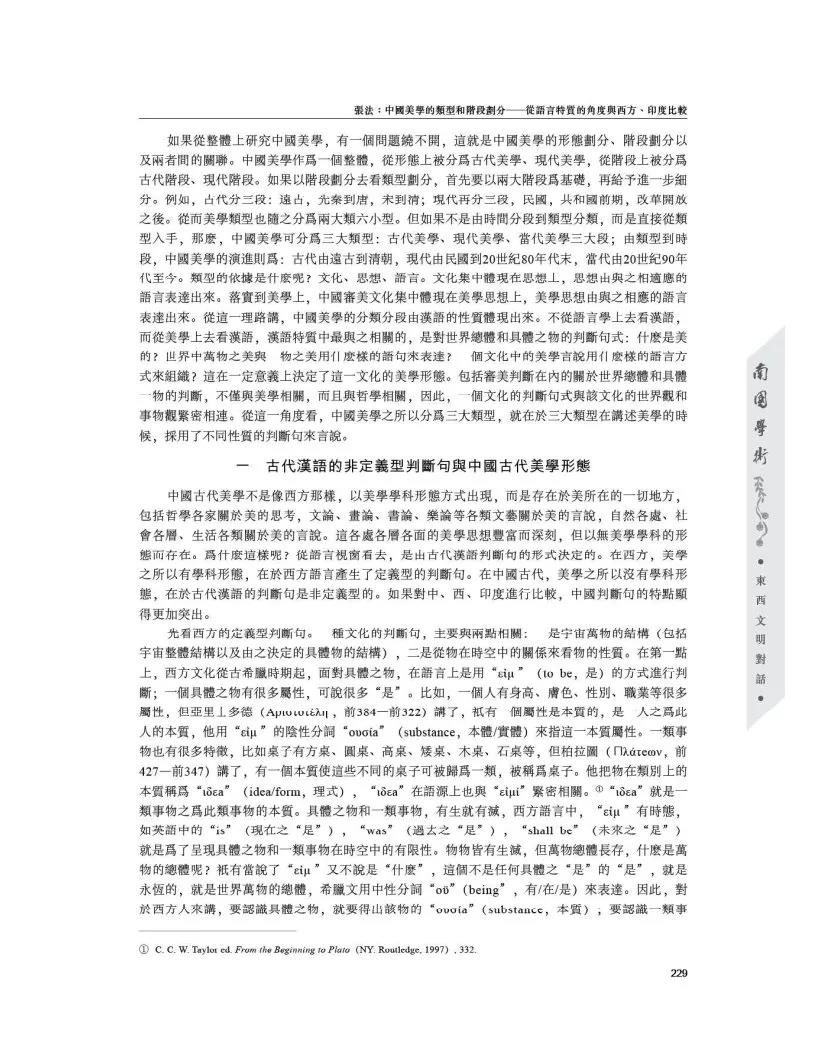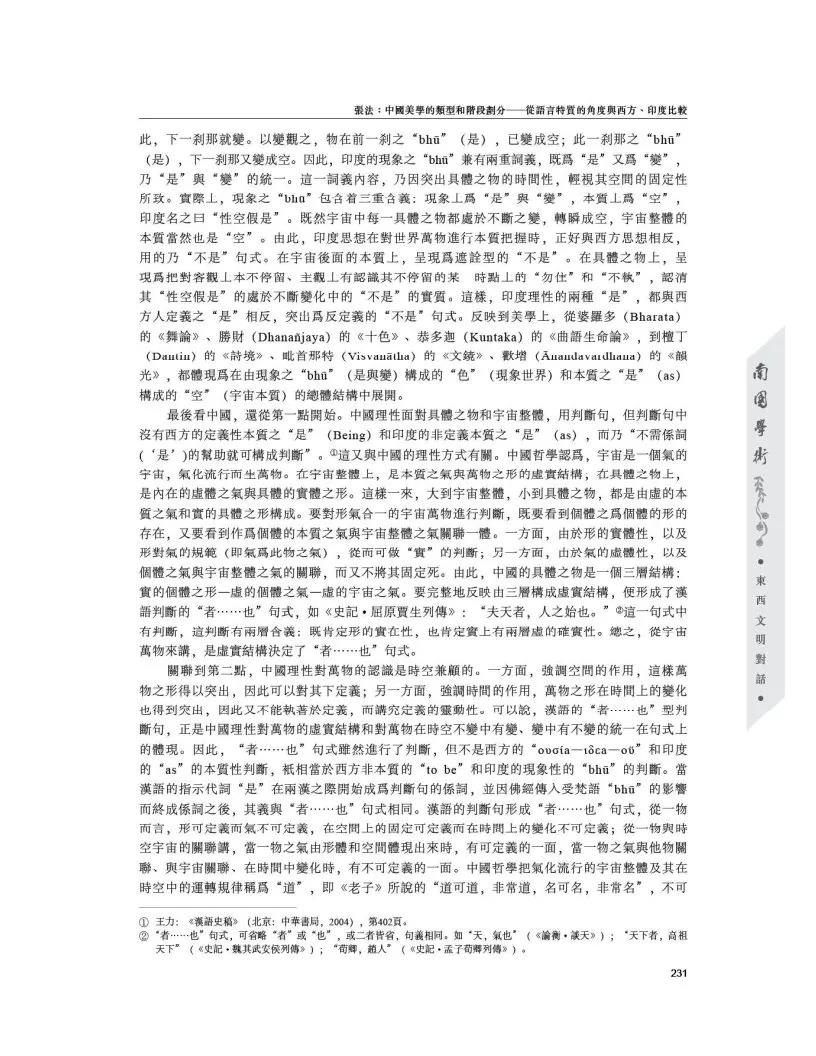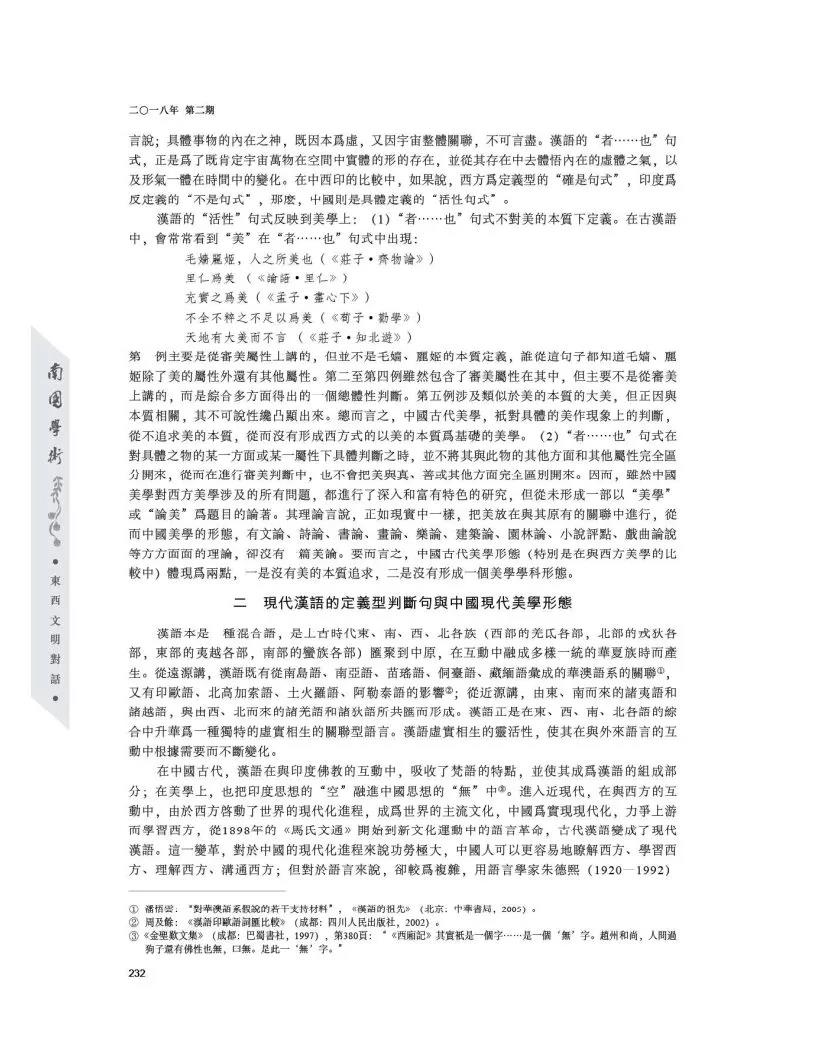——从语言特质的角度与西方、印度比较
张 法
【作者简介】张法,1982年在四川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在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5年在宾州州立大学、1996—1997年在哈佛大学、2002—2003年在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2005年被教育部遴选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美学、审美文化、思想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美学史》《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20世纪中西美学原理体系比较研究》《美学的中国话语》《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等。
【摘要】中国美学可以分为三大形态:以古代汉语为载体的古代美学形态,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现代美学形态,以现代汉语的升级为主的当代美学形态。从古代汉语开始的汉语特质,在与西方语言、印度梵语的比较中,会得到较好的凸显。从语言作为理论的载体来讲,中、西、印的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西方是定义型判断句式,印度是反定义型判断句式,中国是非定义的具体定义判断句式。反映到美学上,中国古代美学,虽然对审美领域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没有关于美的本质定义,也没有形成学科形态的美学。现代汉语在学习西方语言中产生,移植了西方的定义型判断句式,反映到美学上,形成了以美的本质为核心的中国现代美学。随着西方在语言论变革中在哲学上否定了定义型判断语句,在美学上否定了美的本质,中国美学也开始以不追求美的本质而建立美学体系。这样,追求美的本质的中国现代美学转为不以美的本质为核心的中国当代美学,“实践美学”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展望未来,中国当代美学将会在对现代汉语的使用中,在词汇层面,把汉语本有的虚实结合的词性中被压抑的“虚”的一面重新凸显出来,并在词汇活性上突出词与他词的丰富关联;在语句层面,把汉语本有的判断语句上的既有所定又非限制的句义凸显出来,让一个句子虚实相生地与其他句子丰富关联;在体系层面,以词汇和句子的固有性质和生动气韵去灵活形成思想的结构,可以是体系的,也可以是非体系的,并让这一结构与其他结构甚至天地整体形成一种虚实相生的关联,让汉语本有的象外之象、境外之境、韵外之致呈现出来。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未来会形成怎样的景观,是与在全球化的古今中外语言对话中如何进行现代汉语的提升紧密相关的。随着与世界各文化的语言升级进行互动的现代汉语的升级,中国当代美学将会出现新型的美学话语。
【关键词】汉语特质 中西印比较 定义型判断句 中国美学古代—现代—当代形态
如果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美学,有一个问题绕不开,这就是中国美学的形态划分、阶段划分以及两者间的关联。中国美学作为一个整体,从形态上被分为古代美学、现代美学,从阶段上被分为古代阶段、现代阶段。如果以阶段划分去看类型划分,首先要以两大阶段为基础,再给予进一步细分。例如,古代分三段:远古,先秦到唐,宋到清;现代再分三段,民国,共和国前期,改革开放之后。从而美学类型也随之分为两大类六小型。但如果不是由时间分段到类型分类,而是直接从类型入手,那么,中国美学可分为三大类型:古代美学、现代美学、当代美学三大段;由类型到时段,中国美学的演进则为:古代由远古到清朝,现代由民国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代由20世纪90年代至今。类型的依据是什么呢?文化、思想、语言。文化集中体现在思想上,思想由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表达出来。落实到美学上,中国审美文化集中体现在美学思想上,美学思想由与之相应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这一理路讲,中国美学的分类分段由汉语的性质体现出来。不从语言学上去看汉语,而从美学上去看汉语,汉语特质中最与之相关的,是对世界总体和具体之物的判断句式:什么是美的?世界中万物之美与一物之美用什么样的语句来表达?一个文化中的美学言说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组织?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这一文化的美学形态。包括审美判断在内的关于世界总体和具体一物的判断,不仅与美学相关,而且与哲学相关,因此,一个文化的判断句式与该文化的世界观和事物观紧密相连。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美学之所以分为三大类型,就在于三大类型在讲述美学的时候,采用了不同性质的判断句来言说。
一 古代汉语的非定义型判断句与中国古代美学形态
中国古代美学不是像西方那样,以美学学科形态方式出现,而是存在于美所在的一切地方,包括哲学各家关于美的思考,文论、画论、书论、乐论等各类文艺关于美的言说,自然各处、社会各层、生活各类关于美的言说。这各处各层各面的美学思想丰富而深刻,但以无美学学科的形态而存在。为什么这样呢?从语言窗口看去,是由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形式决定的。在西方,美学之所以有学科形态,在于西方语言产生了定义型的判断句。在中国古代,美学之所以没有学科形态,在于古代汉语的判断句是非定义型的。如果对中、西、印度进行比较,中国判断句的特点显得更加突出。
先看西方的定义型判断句。一种文化的判断句,主要与两点相关:一是宇宙万物的结构(包括宇宙整体结构以及由之决定的具体物的结构),二是从物在时空中的关系来看物的性质。在第一点上,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时期起,面对具体之物,在语言上是用“εἰμί”(to be,是)的方式进行判断;一个具体之物有很多属性,可说很多“是”。比如,一个人有身高、肤色、性别、职业等很多属性,但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讲了,只有一个属性是本质的,是一人之为此人的本质,他用“εἰμί”的阴性分词“oυσίa”(substance,本体/实体)来指这一本质属性。一类事物也有很多特征,比如桌子有方桌、圆桌、高桌、矮桌、木桌、石桌等,但柏拉图(Πλάτeων,前427—前347)讲了,有一个本质使这些不同的桌子可被归为一类,被称为桌子。他把物在类别上的本质称为“ιδεa”(idea/form,理式),“ιδεa”在语源上也与“εἰμί”紧密相关。“ιδεa”就是一类事物之为此类事物的本质。具体之物和一类事物,有生就有灭,西方语言中,“εἰμί”有时态,如英语中的“is”(现在之“是”),“was”(过去之“是”),“shall be”(未来之“是”)就是为了呈现具体之物和一类事物在时空中的有限性。物物皆有生灭,但万物总体长存,什么是万物的总体呢?只有当说了“εἰμί”又不说是“什么”,这个不是任何具体之“是”的“是”,就是永恒的,就是世界万物的总体,希腊文用中性分词“oϋ ”(being”,有/在/是)来表达。因此,对于西方人来讲,要认识具体之物,就要得出该物的“oυσίa”(substance,本质);要认识一类事物,就要得出该类事物的“ιδεa”(idea-form,理式);要认识世界整体,就要得出世界整体之为整体的“oϋ”。 具体之物的本质“oυσίa” ,一类事物的本质“ιδεa”,世界整体的本质“oϋ”,都来自或关联到“εἰμί”;从具体之物到世界整体的本质,都用“是”的句式来表达。当说出了本质之“是”,就意味着被说者具有其与之同在的本质。对象的本质之“是”,即对象上“有”本质的,此本质“存在”决定了对象的存在,因此,“oϋ”被中译为“有/在/是”。在认识具体之物到世界整体中说出本质之“oυσίa—ιδεa—oϋ”,构成了西方语言中的本质追求的“是”句式。本质之是的句式,构成了西方文化本质追求的“定义”(definition)句式。对具体之物到世界整体的本质认识,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对其下一个具有本质之是的定义句式。
为什么可以让宇宙整体和具体之物呈现其本质,并对其下一个定义呢?这关联到第二点。西方理性在面对时空中的具体之物时,忽视其在时间中的变化,而强调其在空间中的不变。一个具体之物受时间影响而产生变化的全是非本质属性,在时间中不受其影响而始终不变的即是其本质。所谓本质,所谓定义,就是排除时间影响,只看不变的空间存在,而产生出来的。定义句由内涵和外延组成,内涵即本质,外延即划出时空边界线。边界一划,本质就确定并凸显出来。因此,西方的定义句内蕴着西方理性排除时间影响之后的宇宙整体和具体之物的实体结构。西方思想和句型落实到美学上,就是要对世界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美,下一个关于美的本质的定义;然后从这一美的本质定义出发,推衍出整个美学体系。这正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到英国的夏夫兹伯里(A. A. C. Shaftesbury,1671—1713)、德国的鲍姆加登(A. G. Baumgarten,1714—1762)、法国的巴托(C. Batteux,1713—1780)成形,到康德(I. Kant,1724—1804)、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完成体系化的西方美学的基本特征。
再看印度的判断句。也从第一点开始。印度理性对于世界万物也用“是”的句式进行本质把握,但不像西方那样用一个统一的“εἰμί”(是)生成具体之物、一类事物、世界整体的本质之“是”(oυσίa—ιδεa—oϋ),而是分为两个不同词根之“是”:一个是“as”,表达本质之“是”;一个是“bhū”,表达现象之“是”。与西方把具体之物、一类之物、万物整体都分为现象与本质不同,印度把所有呈现出来的具体之物、一类之物、万物整体都看作“māyā”(幻),世界后面决定世界之为世界的本体在印度教是“Bhaman”(梵),在佛教是“Śūnyatā”(空)。“梵”与“空”本质相通,为了比较上的方便,这里以“空”总括梵与空。与西方在具体之物、一类之物、万物整体的每个层面都区分现象和本质不同,印度把这些都看成是现象之“是”(bhū),由“bhū”所表达的对象,现象为有,本质为幻,从现象上看本质是幻,从本质上看现象是空,因此是性空假有。假有从现象上看又为实有,也有自身的现象本质之分,现象层面的本质,佛教名之曰“samvrti-satya”(俗谛),印度教称其为“saguṇa Brahman”(下梵),包括俗谛、下梵在内的现象世界后面的本体,佛教称之为“paramartha-satya”(真谛),等于空,印度教名之曰“Param Brahman”(上梵),等于梵。真谛之空、上梵之梵在本质上超绝言象,不呈名色。这样对本质层面的陈述,用“as”(是)来表达(如在《犁俱吠陀》中讲宇宙的根本,用“as”的过去式“āsīt”)。但当宇宙的根本演进到梵和空时,其表达的句式就不是说其“是什么”,而是遮诠式地说“不是,也不是,还不是……”。与西方的“是的句式”相反,为“不是句式”。在现象层面,用与“as”本质区别的“bhū”(是),由“bhū”(现象之是)而来的句型,无论用来指具体之物还是指具体之物的俗谛型或下梵型的本质,其本质皆为幻。现象的“bhū”(是)句式表面上为确实之“是”,本质上乃“不是”之空。
为什么印度的本质之“是”和现象之“是”都呈现为“不是”呢?这就关联到第二点,印度理性面对时空中的宇宙万物,轻视空间而强调时间,万物在时间之中都是变化的,此一刹那如此,下一刹那就变。以变观之,物在前一刹之“bhū”(是),已变成空;此一刹那之“bhū”(是),下一刹那又变成空。因此,印度的现象之“bhū”兼有两重词义,既为“是”又为“变”,乃“是”与“变”的统一。这一词义内容,乃因突出具体之物的时间性,轻视其空间的固定性所致。实际上,现象之“bhū”包含着三重含义:现象上为“是”与“变”,本质上为“空”,印度名之曰“性空假是”。既然宇宙中每一具体之物都处于不断之变,转瞬成空,宇宙整体的本质当然也是“空”。由此,印度思想在对世界万物进行本质把握时,正好与西方思想相反,用的乃“不是”句式。在宇宙后面的本质上,呈现为遮诠型的“不是”。在具体之物上,呈现为把对客观上本不停留、主观上有认识其不停留的某一时点上的“勿住”和“不执”,认清其“性空假是”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不是”的实质。这样,印度理性的两种“是”,都与西方人定义之“是”相反,突出为反定义的“不是”句式。反映到美学上,从婆罗多(Bharata)的《舞论》、胜财(Dhanañjaya)的《十色》、恭多迦(Kuntaka)的《曲语生命论》,到檀丁(Dantin)的《诗境》、毗首那特(Visvanātha)的《文镜》、欢增(Ãnandavardhana)的《韵光》,都体现为在由现象之“bhū”(是与变)构成的“色”(现象世界)和本质之“是”(as)构成的“空”(宇宙本质)的总体结构中展开。
最后看中国,还从第一点开始。中国理性面对具体之物和宇宙整体,用判断句,但判断句中没有西方的定义性本质之“是”(Being)和印度的非定义本质之“是”(as),而乃“不需系词(‘是’)的帮助就可构成判断”。这又与中国的理性方式有关。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气的宇宙,气化流行而生万物。在宇宙整体上,是本质之气与万物之形的虚实结构;在具体之物上,是内在的虚体之气与具体的实体之形。这样一来,大到宇宙整体,小到具体之物,都是由虚的本质之气和实的具体之形构成。要对形气合一的宇宙万物进行判断,既要看到个体之为个体的形的存在,又要看到作为个体的本质之气与宇宙整体之气关联一体。一方面,由于形的实体性,以及形对气的规范(即气为此物之气),从而可做“实”的判断;另一方面,由于气的虚体性,以及个体之气与宇宙整体之气的关联,而又不将其固定死。由此,中国的具体之物是一个三层结构:实的个体之形—虚的个体之气—虚的宇宙之气。要完整地反映由三层构成虚实结构,便形成了汉语判断的“者……也”句式,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夫天者,人之始也。”这一句式中有判断,这判断有两层含义:既肯定形的实在性,也肯定实上有两层虚的确实性。总之,从宇宙万物来讲,是虚实结构决定了“者……也”句式。
关联到第二点,中国理性对万物的认识是时空兼顾的。一方面,强调空间的作用,这样万物之形得以突出,因此可以对其下定义;另一方面,强调时间的作用,万物之形在时间上的变化也得到突出,因此又不能执着于定义,而讲究定义的灵动性。可以说,汉语的“者……也”型判断句,正是中国理性对万物的虚实结构和对万物在时空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的统一在句式上的体现。因此,“者……也”句式虽然进行了判断,但不是西方的“oυσίa—ιδεa—oϋ”和印度的“as”的本质性判断,只相当于西方非本质的“to be”和印度的现象性的“bhū”的判断。当汉语的指示代词“是”在两汉之际开始成为判断句的系词,并因佛经传入受梵语“bhū”的影响而终成系词之后,其义与“者……也”句式相同。汉语的判断句形成“者……也”句式,从一物而言,形可定义而气不可定义,在空间上的固定可定义而在时间上的变化不可定义;从一物与时空宇宙的关联讲,当一物之气由形体和空间体现出来时,有可定义的一面,当一物之气与他物关联、与宇宙关联、在时间中变化时,有不可定义的一面。中国哲学把气化流行的宇宙整体及其在时空中的运转规律称为“道”,即《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可言说;具体事物的内在之神,既因本为虚,又因宇宙整体关联,不可言尽。汉语的“者……也”句式,正是为了既肯定宇宙万物在空间中实体的形的存在,并从其存在中去体悟内在的虚体之气,以及形气一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在中西印的比较中,如果说,西方为定义型的“确是句式”,印度为反定义的“不是句式”,那么,中国则是具体定义的“活性句式”。
汉语的“活性”句式反映到美学上:(1)“者……也”句式不对美的本质下定义。在古汉语中,会常常看到“美”在“者……也”句式中出现:
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庄子·齐物论》)
里仁为美 (《论语·里仁》)
充实之为美(《孟子·尽心下》)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知北游》)
第一例主要是从审美属性上讲的,但并不是毛嫱、丽姬的本质定义,谁从这句子都知道毛嫱、丽姬除了美的属性外还有其他属性。第二至第四例虽然包含了审美属性在其中,但主要不是从审美上讲的,而是综合多方面得出的一个总体性判断。第五例涉及类似于美的本质的大美,但正因与本质相关,其不可说性才凸显出来。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美学,只对具体的美作现象上的判断,从不追求美的本质,从而没有形成西方式的以美的本质为基础的美学。(2)“者……也”句式在对具体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属性下具体判断之时,并不将其与此物的其他方面和其他属性完全区分开来,从而在进行审美判断中,也不会把美与真、善或其他方面完全区别开来。因而,虽然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涉及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和富有特色的研究,但从未形成一部以“美学”或“论美”为题目的论著。其理论言说,正如现实中一样,把美放在与其原有的关联中进行,从而中国美学的形态,有文论、诗论、书论、画论、乐论、建筑论、园林论、小说评点、戏曲论说等方方面面的理论,却没有一篇美论。要而言之,中国古代美学形态(特别是在与西方美学的比较中)体现为两点,一是没有美的本质追求,二是没有形成一个美学学科形态。
二 现代汉语的定义型判断句与中国现代美学形态
汉语本是一种混合语,是上古时代东、南、西、北各族(西部的羌氐各部,北部的戎狄各部,东部的夷越各部,南部的蛮族各部)汇聚到中原,在互动中融成多样一统的华夏族时而产生。从远源讲,汉语既有从南岛语、南亚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汇成的华澳语系的关联,又有印欧语、北高加索语、土火罗语、阿尔泰语的影响;从近源讲,由东、南而来的诸夷语和诸越语,与由西、北而来的诸羌语和诸狄语所共汇而形成。汉语正是在东、西、南、北各语的综合中升华为一种独特的虚实相生的关联型语言。汉语虚实相生的灵活性,使其在与外来语言的互动中根据需要而不断变化。
在中国古代,汉语在与印度佛教的互动中,吸收了梵语的特点,并使其成为汉语的组成部分;在美学上,也把印度思想的“空”融进中国思想的“无”中。进入近现代,在与西方的互动中,由于西方启动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力争上游而学习西方,从1898年的《马氏文通》开始到新文化运动中的语言革命,古代汉语变成了现代汉语。这一变革,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功劳极大,中国人可以更容易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理解西方、沟通西方;但对于语言来说,却较为复杂,用语言学家朱德熙(1920—1992)的话来讲,是“把西方语言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大而言之,就是把汉语本来灵活的词性,变成限定严格的词性;把话题—说明型的“者……也”型句式,变为主谓宾的定义型句式;把词句的关联弹性,变成建立在区分上的严格定义。具体到美学上,汉语的“美”字在词性上本来既是客观对象之美(西施之美),又是主体感受的美感(“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现代汉语则把“美”限定在客观对象上,而造一个“美感”来指主体感受。在句式上,有了定义型的句式,这一句式,一是把美的属性与其他属性(如真、善、功利等)区别开来,把美感与其他快感(生理快感、功利快感、伦德快感、知识快感等)区别开来,从而可以形成一个专门的美学学科;二是可以依照西方美学的方式去追求美的本质,成为美学的基础,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出整体美学体系。正是现代汉语的产生,使中国现代美学具有了学科形态。中国现代美学也正式从清末的王国维(1877—1927)、蔡元培(1868—1940)、梁启超(1873—1929)、刘师培(1884—1919)开始,到五四时代有了体系性的美学原理著作的出现。
从清末到五四,在现代汉语击败古代汉语的背景中,一种新型的中国现代美学产生了出来。这一中国美学的新类型从语言上讲,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通过西方美学新词汇的引进和对古代汉语中旧语的改造,形成中国现代美学的新语汇。第二,形成定义型判断句。在第一点上,最重要的是西方的“aesthetics”在汉语中被定型为“美学”。肯定“美学”这一新词,不仅是肯定与美相关的思想要有一种“学”(学科形态),而且要确立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组织方式。这就是,要以定义型的判断句作为美学学科的核心。在美学进入之初,蔡元培、王国维虽然仍用古代汉语讲西方美学,但已经把西语中定义型判断句的精神灌注到古代汉语中去了: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壮之对象,汗德(康德——引者注)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就美术(艺术——引者注)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于形式, 固不俟矣,即图画、诗歌之美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美感——引者注)故,故亦视为一种形式焉。
美学观念者,基于快与不快之感,与科学之属知见,道德之发于意志者,相为对待。科学在乎探究,故论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首鉴赏,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是吾人意识发展之各方面也。
当现代汉语成为主流之后,在美学著作中,定义型判断句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地清晰:
美学乃研究关于人类理想之一就是美的理想方面的法则之科学。
美……乃是由感情移入而成立的物象的价值。
美的学问——即美学——底对象,共有(一)美,(二)自然,人体,艺术,(三)美感,美意识等三方面。
美是人们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及其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美是一个感性的具体存在,它一方面是一个合规律的存在,体现着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又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所以美是饮食或体现社会生活本质规律,能够引起人们特定情感反映的具体对象(包括社会形象,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
定义型判断句在学术著作中出现和定型,同时展开两方面要求:一方面,在词汇上进一步要求对进行定义型话语的每一概念转到西方式的实体性定义,把古代汉语的虚实合一的灵动之词转为西方语词的实体性可定义之词,这极大地促成了现代汉语意义上的美、美感、艺术、形象、客观、主观、规律等美学语汇完全具备了与西方语汇的对应内容和形成;另一方面,又要求理论体系向西方的学科化、逻辑化、体系化方面发展。正是这后一方面,定义型判断句在现代学术产生、演进、形成进程中,西方学科型的美学原理著作开始出现。例如,萧公弼写的《美学概论》 1917年连载于《寸心》杂志(共出了6期,未完);吕澄1923年1月出版现代中国第一部完整内容的《美学浅说》,12月再出版名称严肃的《美学概论》;然后,有陈望道编着《美学概论》(1927)、范寿康编《美学概论》(1927)、徐庆誉《美的哲学》(1928)等等;最重要的是朱光潜借鉴综合西方审美心理诸流派,写成了《文艺心理学》(1931年写成,1936年出版)、《谈美》(1932),真正完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中体系性的美学理论著作。同时,意味着中国美学的现代形态在定义型判断句—实体性语汇—体系性结构这三方面的完成。这三者是一体的,定义型的判断句,必然要求实体型的语词词汇,也必然要求体系化的展开。而这三个是否达到西方学术的标准,成了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在朱光潜(1897—1986)以西方美学为参照、成就中国美学现代形态之时,苏俄美学影响日增。周扬(1907—1989)、蔡仪(1906—1992)等与苏联美学互动,周扬写了《我们需要新美学》(1937)一文,蔡仪写成体系性的专著《新美学》(1947)。苏俄美学与西方美学虽然在思想内容上不同,但在美学思想的语言表述方面是一致的,都要有定义型判断句立起一个学科的中心(在美学上就是美的本质的定义),要有与之相应的实体性语汇群充实这一学科的骨肉(在美学上就是要有一批基本美学范畴语汇),要以逻辑的展开完成自身体系(在美学上就是要展开为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等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如果说,在民国时期,朱光潜美学代表了西方美学对中国的影响,蔡仪美学代表了苏俄美学对中国的影响,那么,1949年后,美学要形成与共和国思想相适应的新形态,于是从1950—1960年代,就有了关于美的本质大讨论。这一讨论从语言上看,不是要改变定义型判断句的形式,而是要更新定义型判断句的内容。这时,关于美的本质定义的判断句出现了四种不同的内容:(1)蔡仪的美的本质判断句:美是客观的。(2)高尔泰、吕荧的美的本质判断句:美是主观的。(3)朱光潜的美的本质判断句:美是主客观的统一。(4)李泽厚的美的本质判断句: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有了四种不同的本质定义判断句,就树立起了四种不同的美学思想大旗,后来的学术史家因之称为美学四派。为什么一篇或几篇文章就可以成派?因为,美的本质判断句的不同内容,已经内蕴着要产生与之相应的美学词汇群,要以判断句和词汇群来展开自己的体系,而且后来果然产生了成派的体系硕果:蔡仪主编了《新美学》(三卷改写本1985—1999),高尔泰出了《论美》(1982),朱光潜推出《谈美书简》(1981),李泽厚发表《美学四讲》(1989)。虽然四派的本质定义型判断句的内容不同,但这不同的内容都用本质定义型判断句来表现(并且产生了实体性语汇群和逻辑性体系结构)。正是这一本质定义型判断句,成了中国美学之现代形态的标志。以此为标志,可以把中国美学的现代形态分为三类:一是民国时代朱光潜受西方美学影响的现代形态,二是民国时代蔡仪受苏俄美学影响的现代形态,三是共和国前期四种本质定义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完成体系的现代形态。这一时期的种种论著,都可以归结到这三种美学的现代形态之中。
三 西方定义型判断句的衰落与中国美学的形态转变
中国美学在从古代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向西方古典美学学习,取得了基本成就,有了美学的学科形态。从语言的角度看,与西方古典美学一样,有了定义型判断句—实体性语汇群—体系性结构。但是,其行进甚为艰难。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花了八十多年,才以四派的体系型著作为标志,完成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形态。但当其正走向完成之时,已到改革开放之初,突然发现,西方美学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即从西方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的变化。如果说,西方古典美学是以定义型判断句为美学学科的核心,那么,西方现代美学则否定了这一核心。西方美学对自身的否定,一方面与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有关,包括西方科学从古典物理学向现代物理学、从欧氏几何型向非欧几何型、从牛顿型向爱因斯坦型的多重转变,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后现代的演进;另一方面,与各非西方文化的对话有关,西方科学、哲学演进得出的结果越来越与非西方文化思想,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思想具有质的相似。西方美学正是在这一整体的文化演进中,从古典走向了现代,走向了对由定义型判断而来的美的本质定义的否定。这一否定坚定有力,对中国美学向新形态的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的否定,具体路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的词性给人以误导,二是美的句型给人以误导,三是区分型的体系方式给人以误导。
——词性方面。人在审美时,在语言上表述为:某物是“美的”,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形容词一般地是由相应性质的名称引伸转成的”,从而“美的”这一形容词具有名词功能,是指某物的属性。但是,维特根斯坦(L. J. J. Wittgenstein,1889—1951)、艾耶尔(A. J. Ayer,1910—1989)却发现,“美的”这一形容在具体审美中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进而细辩,方悟“美的”其实是一个不指属性而只表主体感受的感叹词——面对美丽的晚霞,说“晚霞是美的”与说“晚霞真美”和说“晚霞,啊!”表达的意思相同,三个可以互换而意义不变。如果我们对一个女人、一幅画、一个花瓶等不断地说“是美的”,然后就去寻找决定这些事物为美的这个“美的”本质,那么,为什么在对以前事物一一说“啊”之后,不去寻找“啊”的本质呢?实质在于:受了“美”这个词的误导。从理论的严格性讲,如此讲“词性”并非没有问题,比较一下古汉语对“美”字的解释可知此问题的复杂性。但在西方的语言逻辑中,词性说又是很有力的,更在于美的本质本身有问题,因此,词性之辩成为否定美的本质的一颗重弹。
——句型方面。肯尼克(W. E. Kennick,1923—2009)发现,语言的定义句型应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问题。例如,氦是什么?可给一个定义性回答:氦是一种化学元素,气态,惰性,无色,原子序数2,原子量4.003。科学的定义一旦给出,就成定论。另一类是哲学问题。例如,美是什么?哲学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一旦给出,终会被证伪,正如美学史上关于美的本质的定义一样。然而,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拥有相同的句型,由于人们在科学之问上屡屡成功,就误认为在哲学之问上也可以成功,这是受了句型的误导。这样讲句型,从理论的严格性说并非没有问题,比较一下印度于对“as”(本质之是)和“bhū”(现象之是),可知句型问题的复杂性。但在西方的语言逻辑中,句型说又是很有力量的,更在于美的本质本身有问题,因此,句型之辩成为否定美的本质的又一颗重弹。
——体系方式。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家族相似”:一个家族的各成员皆相似,但兄与弟的眼相似,弟与妹的鼻相似,妹与姐的身材相似,以此类推,但不能说某一特征是覆盖所有成员的共同特征。因此,一个家族的生理本质是不能用某一个或几个特征来定义的,从而是不能用一个定义型判断句来表述的。美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个相似家族。它是一些或某些特征的不断出现和消失,但无法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征放进定义型判断句,或者下一个本质定义。维特根斯坦用西方逻辑讲出了用定义型断句下本质定义和方式去呈现一个体系的困难。从理论的严格性讲,这一论述方式并非没有问题,将之与中国理性、印度理性如何结构体系的方式进行比较就很清楚。但因美的本质本身有问题,因此“家族相似”也成为否定美的本质的一颗重弹。
总而言之,西方现代美学以分析美学为代表与其他流派一起否定了美的本质。从语言上讲,否定了定义型判断句在理论中的核心作用。这一西方美学转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美学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国美学史;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在民国时代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宗白华(1897—1986)、邓以蛰(1892—1973)、方东美(1899—1977)的研究中,但却没有写成中国美学史的通史著作,因为,面对中国美学史的材料,无法以美的本质为中心形成整体叙述;而在西方转型后的理论话语影响下,可以不用美的本质为中心,而以各种美学问题为重点,进行整体叙述,于是中国美学的通史著作,从李泽厚和刘纲纪《中国美学史》(1984—198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1989)开始,一部部地出现了。在美学原理上,渐渐地不给美的本质下定义,而以美学问题为重点,讲清一个个的问题,成为了主流。
如果说,20世纪的前七十多年的中国美学,都是要求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型判断句来给美的本质下定义,然后以此为中心来建立美学体系,可称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形态,那么,放弃定义型判断句的中心地位,不追求美的本质而建构美学理论,就可名之为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中国美学从现代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变,最明显地体现在实践美学上。实践美学的前身,是20世纪50—60年代美的本质大讨论中的“社会派”,即认为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派”,在定义美的本质时,转动态(客观性加上社会性,“加”是一个动态)为静态(加上后的结果为静)。80年代以后,他由“社会派”升华为“实践派”,实际上是把定义的静还原为形成的动,并将之凸显出来;客观性与社会性之“加”,在于人的实践活动,而且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以实践为核心来看美,人在实践中,一方面,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了自己的对象世界(这就是审美对象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产生对象世界(美的世界)的同时,产生了与之对应的心理世界(审美心理结构)。这样,社会派就成为了实践派。“社会派”强调的是美的本质(美感的本质在此之上而产生),“实践派”则强调的是由实践同时产生美和美感。虽然实践派不断地在给美的本质下定义,但由于以人作为主体的实践为中心,必然是美和美感的同时进行,美的本质在逻辑上已经成了一个次要问题。同时,实践美学以人的主体实践为核心,实践既可以作为物质生产的实践(这一点与社会派美学的联系较为紧密,李泽厚本人都不时情不自禁地回到这一点上去),也可以作为精神生产生的实践(在这一点上进行强化,朱光潜的美学也以此成为一实践美学)。正因为以主体的实践为主轴,可以有多方向的延展,从而中国的实践美学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支派:李泽厚型的实践美学,刘纲纪型的实践美学,蒋孔阳型的实践美学,朱立元型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张玉能型的新实践美学,邓晓芒型的新实践美学……
在实践美学的多方向展开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凸显出来:实践美学如果要得出一个美的本质定义,那么,这一定义在美学体系中无法逻辑地成为统帅一切的核心;如果实践美学不得出一个美的本质的定义,并不影响由之而来的美学体系的建立。这说明了,实践美学兼有可得出可不得出美的本质定义,正好作为中国美学历史演进中从追求美的本质到不追求美的本质的过渡。因此,可以说,正是实践美学的多面展开中,以及与之同时出现的各种非实践美学中,中国的美学形态发生了阶段性变化,进入了当代美学形态,即不用定义型判断句去追求美的本质而建立美学体系的时期。用定义型判断句形成的美的本质的有无,来区分中国美的现代形态和当代形态,中国美学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以来的美学演进逻辑就清楚了。
四 定义型判断句的转义与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
从以定义型判断句追求美的本质为核心建立美学体系的中国美学现代形态,转型到不追求美的本质而建立美学体系的中国美学当代形态,直接的契机是西方现代美学否定了美的本质,但其中也内蕴着现代汉语的演进。汉语由古代汉语转为现代汉语,虽然出现以系词“是”为标志的定义型判断句式,构成学术话语的主干,但“是”一直存在于古代汉语的非定义型句式中,也仍然存在于现代汉语的非定义性句式中。可以说,西方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正与古代汉语中的“是”的非定义型句式相合。而实践美学的可以定义美的本质/也可以不定义美的本质,也与汉语中“是”句型可以在定义型判断句式和非定义型判断句式之间“软性游走”极为相关。只是现代汉语与西方现代美学在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述上的迎合,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料。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美学因为不以定义型判断句为核心去建立自己的体系,标志了中国美学从现代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折,但当代美学形态会以何种方式演进,这种演进会形成怎样的特征,还难以预料。正如西方美学从古典形态转到现代形态之后,放弃定义型判断句的中心地位,意味着西方语言的实体性感受到自身的局限。西方的实体性语言不可能转向汉语的虚实结构,而只能呈现为维特根斯坦型的“游戏方式”、德里达型的“分延方式”、德勒兹型的“游牧方式”……而现代汉语的实体性,本是从古代汉语的虚实结构转来,并且是在西方的定义型判断句的强力支持下转过来的,一旦失去了定义型判断句的强力压制,本来存在于汉语中的虚实结构就会重新冒出来。这时,现代汉语将产生一种新的转变和提升。
在西方,与思想转型相伴随的是语言转型,只是体现在定义型判断句和与之相适应的完整体系性上,而并未影响到词汇的实体性质。如果说,理论的语言表达需要判断句—词汇—体系这三者的一致,那么,西方理论的语言表述在判断句式和体系结构上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只是在实体性语汇上尚未变化。正是判断句式、体系结构与实体语汇之间的矛盾,使得西方的思想演进还处在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难以自拔。也因此,从西方思想进入现代开始,“隐喻”(metaphor)一词就成了到处弥漫的概念,力图解救一种难以解救的困窘。每当西方的实体性词汇明显出错而隐入困境时,理论就会改口说,这一词汇不能按字面去理解,而要按隐喻去领会。在中国,初看起来,汉语在古代时本有的虚实结构,包括在词汇上和判断句上的虚实结构,会使现代汉语容易摆脱西方实体性语言正在遭遇的困境,而在实际上,也许现代汉语面临的困境比西方语言还要严重。这是因为,一方面,汉语在从古代的虚实结构转为现代的实体结构之时,自身有一系列困难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已经基本定型的现代汉语在应对西方由思想转变所产生的语言变动,又有一重困难。现代汉语是在双重困难中,面临着西方思想转向所带来的冲击。
西方美学从20世纪以前的古典形态进入到20世纪后,相继呈现了两种形态,即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而在这两种形态之中,还包含着另一形态。这一形态最初是以隐形方式内蕴于现代美学之中,在进入后现代美学时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全球化形态。它是包含着很多非西方文化因素于其中的美学,或者说,是在与非西方文化互动中而产生的美学形态,因此,也可以把西方美学的三种形态,即现代美学、后现代美学、全球化美学合称为“西方当代美学”。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中国当代美学在与西方当代美学的互动中,从语言角度看,仍会像19世纪后期那样,受着三个方面的影响:判断句式—词汇性质—体系结构。如果说,在当时,汉语的古今之变,全方位地吸收西方语言的实体词性—定义型判断句—体系结构的基础上,让汉语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取得了与西方语言在基本方面的一致,从而在推进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包括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么,在这一次从现代美学向当代美学的转型中,中国美学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环顾当今世界,由于正在转型的西方思想遇上了自身语言的局限,在实体性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西方语言不对世界的其他语言如汉语、梵语本有的特质进行很好的吸收,要想走出自身困境相当困难;同样,面对世界主流思想的转型,中国现代思想不对自身的现代汉语,站在世界思想史、语言史的高度进行反思,要让已经起程了的中国当代美学建立应有的形态,也有相当的困难。在西方,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形式美理论等对西方以艺术为核心的美学主流的批判,尚在胜负未分的缠斗之中,里面既有思想的艰难,也有语言的困扰。在中国,一方面,在与西方美学的互动中,同样有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的兴起;另一方面,原有的实践美学、非实践美学也在按自身的方向演进。从这一角度看,各种各样的中国当代美学,将会怎样思考自身的语言表述,提升自己的语言方式,这是一个待解的难题。展望未来,中国当代美学需要在对现代汉语的使用中,在词汇层面,把汉语本有的虚实结合的词性中被压抑的“虚”的一面重新凸显出来,并在词汇活性上突出词与他词的丰富关联;在语句层面,把汉语本有的判断语句上的既有所定又非限制的句义凸显出来,让一个句子虚实相生地与其他句子丰富关联;在体系层面,以词汇和句子的固有性质、生动气韵去灵活形成思想的结构,可以是体系的,也可以是非体系的,并让这一结构与其他结构甚至天地整体形成一种虚实相生的关联,让汉语本有的象外之象、境外之境、韵外之致呈现出来。从语言角度讲,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会形成怎样的景观,是与在全球化的古今中外语言对话中如何进行现代汉语的提升紧密相关的。在这一意义上,对中国美学进行形态的划分,并在这一划分中突出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有利于中国当代美学的文化自觉。
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2期第227—238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烦请继续向下拉,就可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