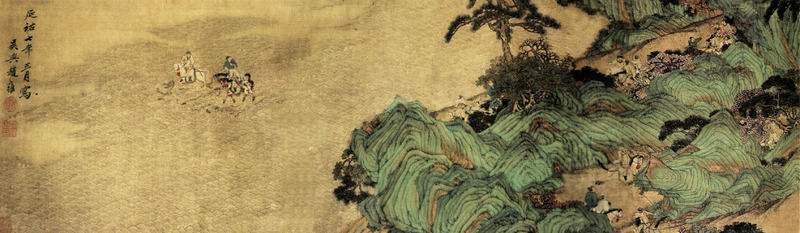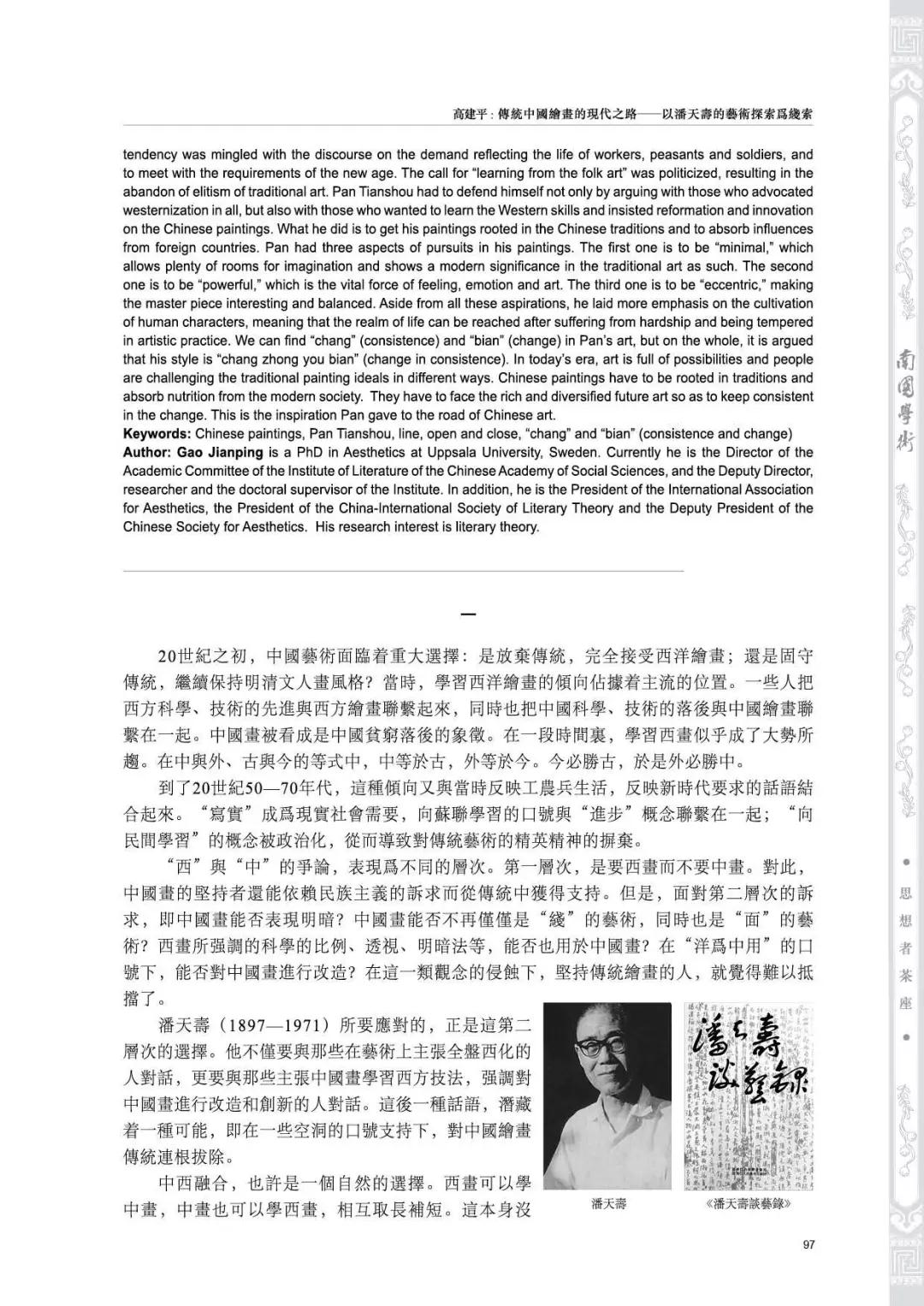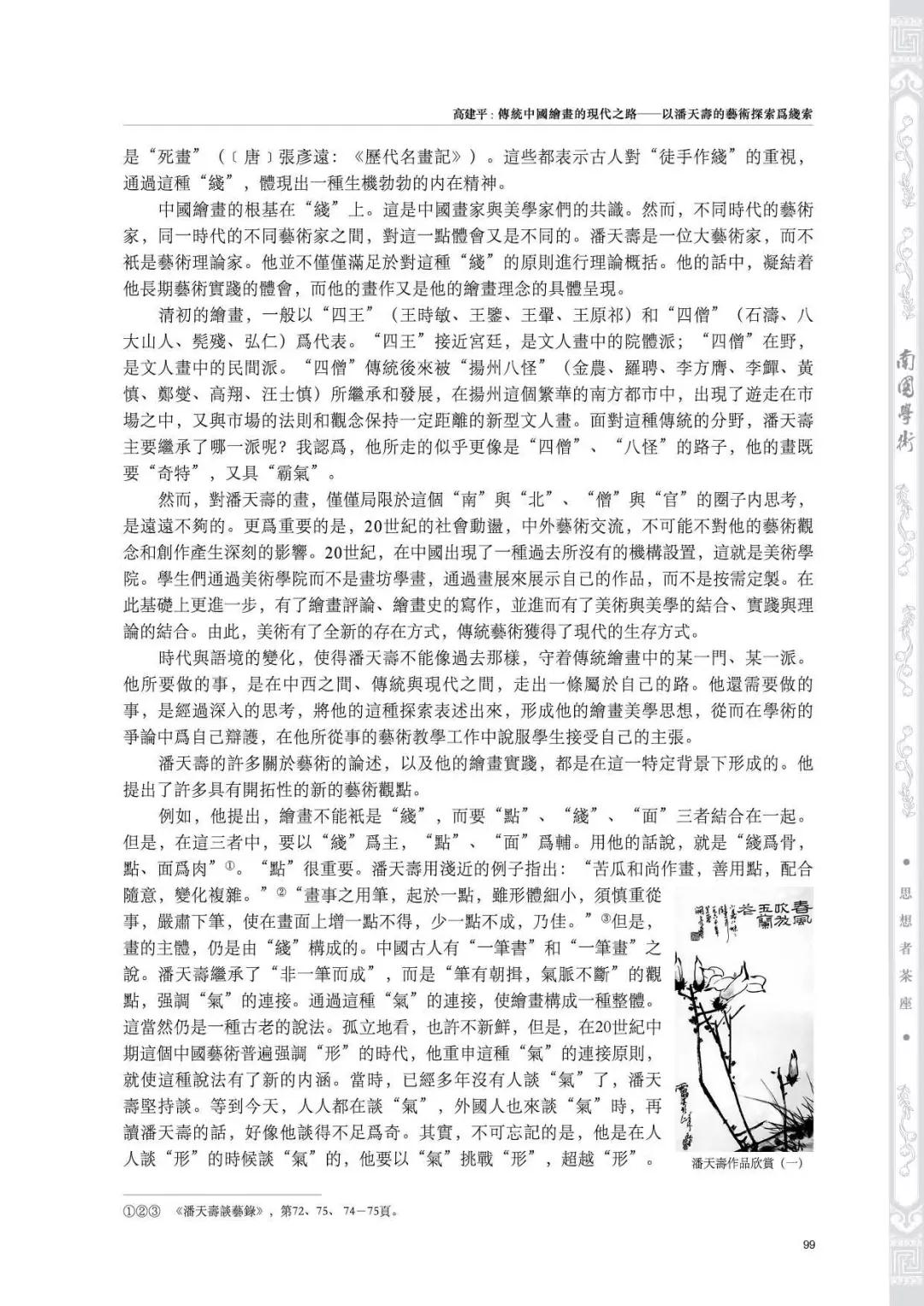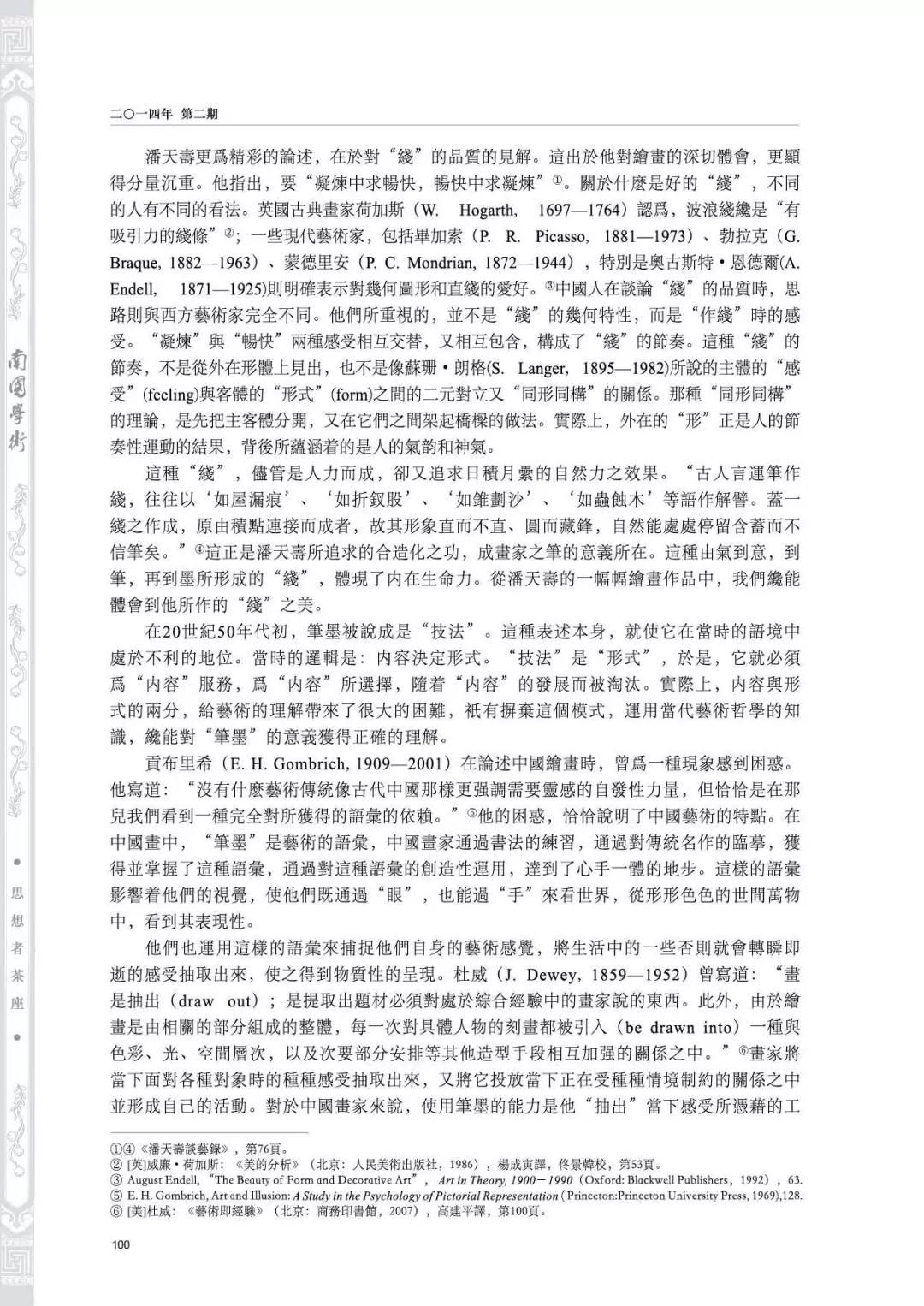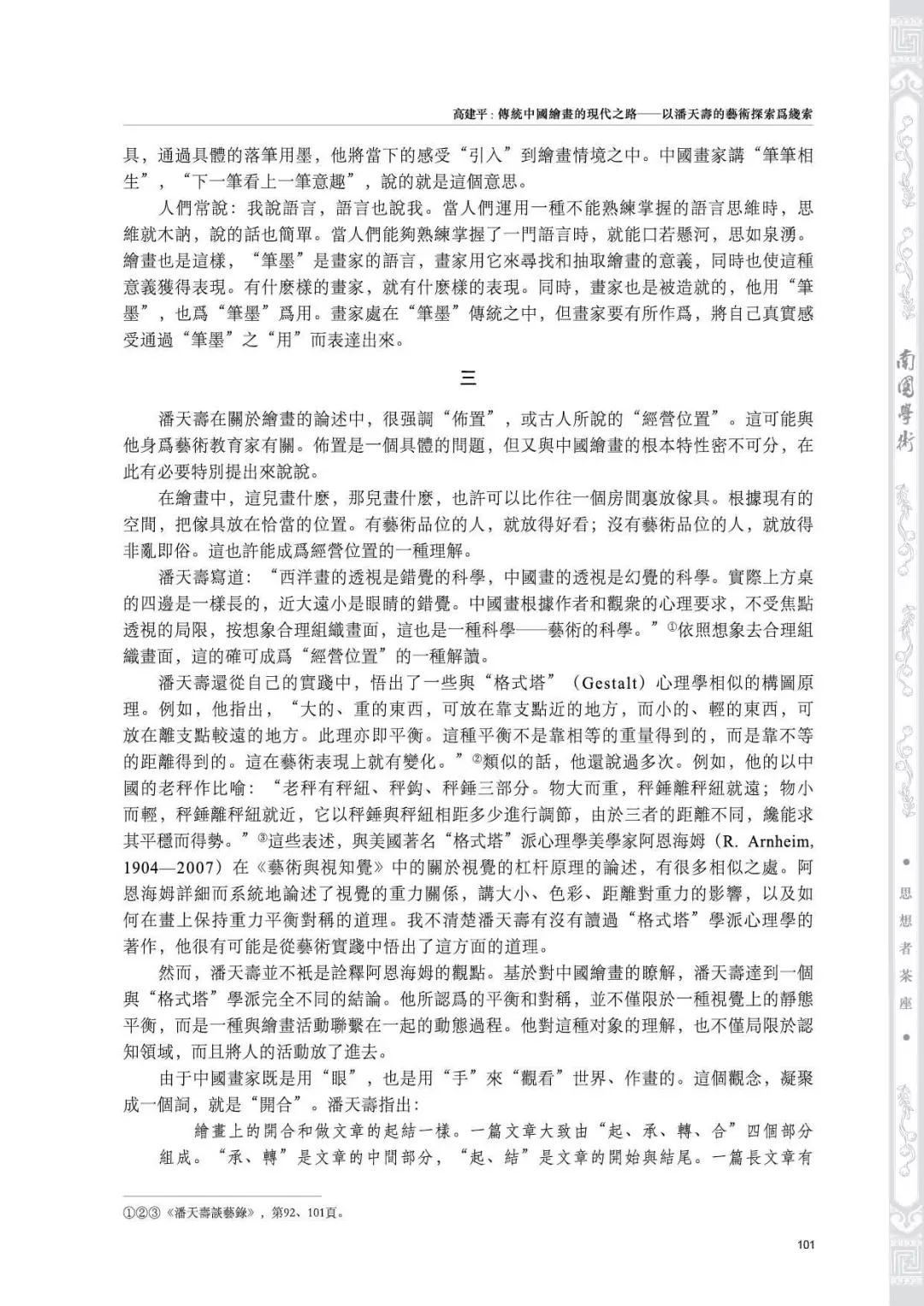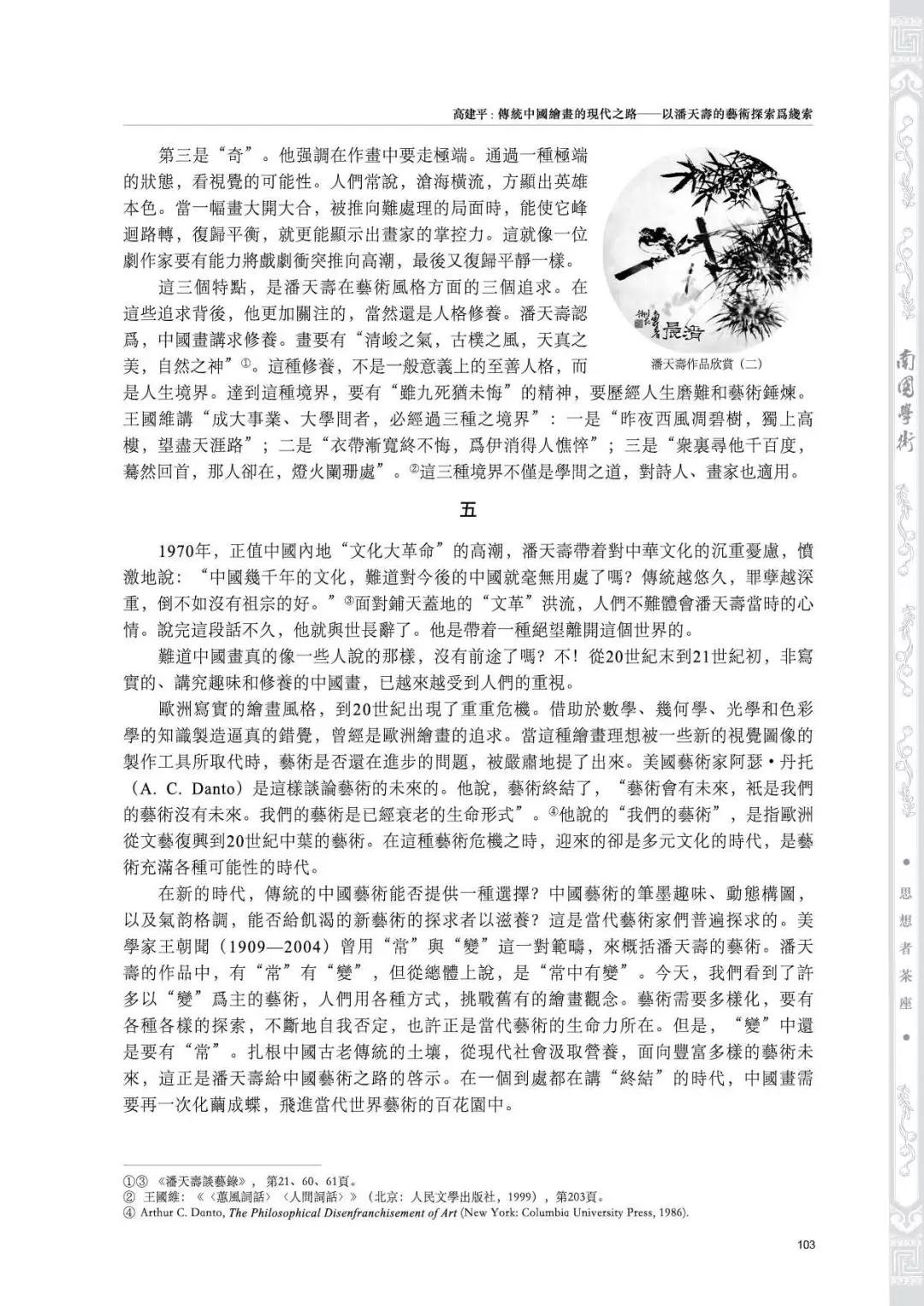[作者简介]高建平,1984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6年在乌普萨拉大学获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副所长、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代表性著作有The Expressive Act in Chinese Art:From Calligraphy to Art、《画境探幽——中国绘画的精神结构》《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文化》,译著有《艺术与精神分析》([美]斯佩克特)《先锋派理论》([德]比格尔)《西方美学简史》([美]比厄斯利)《艺术即经验》([美]杜威)等。
传统中国绘画的现代之路
——以潘天寿的艺术探索为线索
摘要:20世纪之初,一些人把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西方绘画联系起来,中国画被看成是中国贫穷落后的象征,学习西画似乎成了大势所趋;到了20世纪50—70年代,这种倾向又与当时反映工农兵生活、反映新时代要求的话语结合起来,“向民间学习”的概念被政治化,从而导致对传统艺术的精英精神的摒弃。潘天寿不仅要与那些在艺术上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对话,更要与那些主张中国画学习西方技法,强调对中国画进行改造和创新的人对话。他的做法是,根植传统,以我为主地对外来影响进行吸收。潘天寿在艺术风格方面有三个追求:一是“简”。通过“简”,留下广泛的想象空间,也在传统风格的艺术中见出现代意味。二是“力”。这个“力”是力能扛鼎,是作品的气之力、情之力、艺之力。三是“奇”。通过一种大开大合,使它峰回路转,复归平衡。在这些追求背后,他更加关注的还是人格修养——历经人生磨难和艺术锤炼的人生境界。潘天寿的作品中有“常”有“变”,但从总体上说是“常中有变”。在当今艺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到处都在讲“终结”的时代,人们用各种方式挑战旧有的绘画观念,中国画需要扎根古老传统的土壤,从现代社会汲取营养,面向丰富多样的艺术未来,“变”中有“常”。这是潘天寿给中国艺术之路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绘画 潘天寿 线 开合 “常”与“变”
一
20世纪之初,中国艺术面临着重大选择:是放弃传统,完全接受西洋绘画;还是固守传统,继续保持明清文人画风格?当时,学习西洋绘画的倾向占据着主流的位置。一些人把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西方绘画联系起来,同时也把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与中国绘画联系在一起。中国画被看成是中国贫穷落后的象征。在一段时间里,学习西画似乎成了大势所趋。在中与外、古与今的等式中,中等于古,外等于今。今必胜古,于是外必胜中。
到了20世纪50—70年代,这种倾向又与当时反映工农兵生活,反映新时代要求的话语结合起来。“写实”成为现实社会需要,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与“进步”概念联系在一起;“向民间学习”的概念被政治化,从而导致对传统艺术的精英精神的摒弃。
“西”与“中”的争论,表现为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要西画而不要中画。对此,中国画的坚持者还能依赖民族主义的要求而从传统中获得支持。但是,面对第二层次的要求,即中国画能否表现明暗?中国画能否不再仅仅是“线”的艺术,同时也是“面”的艺术?西画所强调的科学的比例、透视、明暗法等,能否也用于中国画?在“洋为中用”的口号下,能否对中国画进行改造?在这一类观念的侵蚀下,坚持传统绘画的人,就觉得难以抵挡了。
潘天寿(1897—1971)所要应对的,正是这第二层次的选择。他不仅要与那些在艺术上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对话,更要与那些主张中国画学习西方技法,强调对中国画进行改造和创新的人对话。这后一种话语,潜藏着一种可能,即在一些空洞的口号支持下,对中国绘画传统连根拔除。
中西融合,也许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西画可以学中画,中画也可以学西画,相互取长补短。这本身没有错。然而,究竟如何学?在融合的过程中,到底以什么为基础,以什么为附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潘天寿的主张是:“西画,还是应在西画的基础上搞,不必插入其他的东西。”相反,“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绘画差不多,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传统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相比,在审美理想上有着根本的差异。当然,若硬要将其混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在百花齐放的艺术大花园中,也能成为一朵奇葩。但是,正像驴与马交配后能生出孔武有力的骡子一样,虽具实用性但却不具生产性。对于中国绘画传统的保存和发展,这种非驴非马的混杂却可能会是致命性的破坏。在交融的名义下,中西结合可能会成为一种过渡,但其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国艺术传统的消亡。
那么,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语境下,中国艺术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呢?潘天寿认为,对外来传统,“亦须细心吸取,丰富营养”。欧洲绘画长期形成的对“线”“形”“色”的理解,艺术表现的多种技巧,应该成为发展中国画的营养。其实,不仅仅欧洲绘画,世界其他各民族的绘画、雕塑和其他造型艺术,都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然而,学习借鉴,还要依据主体情况而有所选择。他提出吸收和发展的“以我为主”的原则,“有所不融和者,应不予吸收”。对此,潘天寿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牛奶是营养的,但中国人吃了不要就变成外国人,中国人的形体不能失了。”我们要持一种有“体”有“用”的立场。中国画有着自身的“体”,失去了,就不再是中国画;也有其“用”,要吸收西画的一些长处,丰富自身。
其实,不同民族的艺术,都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文化间相互交流的立场,故步自封不行;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在美学上,有过关于世界上有统一而普遍的美,还是各民族和文化只是独特美的争论。对此,我认为:一方面,从来就没有单一而普遍的美。各民族、各文化都自美其美。各民族和文化的审美趣味,是特定文化和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又是相互联系着的,就像相互补充营养一样,各民族和文化间要相互学习。因此,独存又共存,自主创新又相互吸收,不要普遍主义,不要折衷主义,根植传统,面向世界,这才是艺术发展之道。
二
民族文艺的根基不能丧失。具体落实到绘画,根基到底在哪里呢?宗白华(1897—1986)曾作过一个精要的概括:“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于一境层。西画以建筑空间为间架,以雕塑人体为对象,建筑、雕刻、油画同属于一境层。”潘天寿则反复强调,中国绘画以“线”为主,西方绘画以“面”为主。
由此,人们或许要进一步追问:中国画的“线”是什么样的“线”?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即中国画的“线”是“徒手作出来的线”,而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线”,以此强调中国艺术对动作性的重视,并试图说明中西绘画区分的一些根本问题。
无论是潘天寿所强调的笔墨,还是他所作的指画,都与手的动作有关。在绘画中,要见出人的动作,要将绘画看成是人的充满活力的动作的痕迹。中国古代有“书画同源”之说。许多人在读这句话时,把着眼点放在历史起源上,相信书与画在历史上真的曾有过一个“同体未分”的状态,只是到后来两者才分化开来。其实,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这个表述无非是强调书法的“线”对绘画的“线”的影响而已。许多古人还强调,最好的画要“拙规矩于方圆”(﹝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不能用界笔直尺,用这些制图工具作出的画是“死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这些都表示古人对“徒手作线”的重视,通过这种“线”,体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内在精神。
中国绘画的根基在“线”上。这是中国画家与美学家们的共识。然而,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同一时代的不同艺术家之间,对这一点体会又是不同的。潘天寿是一位大艺术家,而不只是艺术理论家。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这种“线”的原则进行理论概括。他的话中,凝结着他长期艺术实践的体会,而他的画作又是他的绘画理念的具体呈现。
清初的绘画,一般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和“四僧”(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弘仁)为代表。“四王”接近宫廷,是文人画中的院体派;“四僧”在野,是文人画中的民间派。“四僧”传统后来被“扬州八怪”(金农、罗聘、李方膺、李鳝、黄慎、郑燮、高翔、汪士慎)所继承和发展,在扬州这个繁华的南方都市中,出现了游走在市场之中,又与市场的法则和观念保持一定距离的新型文人画。面对这种传统的分野,潘天寿主要继承了哪一派呢?他所走的似乎更像是“四僧”“八怪”的路子.他的画既要“奇特”,又具“霸气”。
然而,对潘天寿的画,仅仅局限于这个“南”与“北”、“僧”与“官”的圈子内思考,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的社会动荡,中外艺术交流,不可能不对他的艺术观念和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20世纪,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的机构设置,这就是美术学院。学生们通过美术学院而不是画坊学画,通过画展来展示自己的作品,而不是按需定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绘画评论、绘画史的写作,并进而有了美术与美学的结合、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由此,美术有了全新的存在方式,传统艺术获得了现代的生存方式。
时代与语境的变化,使得潘天寿不能像过去那样,守着传统绘画中的某一门、某一派。他所要做的事,是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还需要做的事,是经过深入的思考,将他的这种探索表述出来,形成他的绘画美学思想,从而在学术的争论中为自己辩护,在他所从事的艺术教学工作中说服学生接受自己的主张。
潘天寿的许多关于艺术的论述,以及他的绘画实践,都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新的艺术观点。
例如,他提出,绘画不能只是“线”,而要“点”“线”“面”三者结合在一起。但是,在这三者中,要以“线”为主,“点”“面”为辅。用他的话说,就是“线为骨,点、面为肉”。“点”很重要。潘天寿用浅近的例子指出:“苦瓜和尚作画,善用点,配合随意,变化复杂。”“画事之用笔,起于一点,虽形体细小,须慎重从事,严肃下笔,使在画面上增一点不得,少一点不成,乃佳。”但是,画的主体,仍是由“线”构成的。中国古人有“一笔书”和“一笔画”之说。潘天寿继承了“非一笔而成”,而是“笔有朝揖,气脉不断”的观点,强调“气”的连接。通过这种“气”的连接,使绘画构成一种整体。这当然仍是一种古老的说法。孤立地看,也许不新鲜,但是,在20世纪中期这个中国艺术普遍强调“形”的时代,他重申这种“气”的连接原则,就使这种说法有了新的内涵。当时,已经多年没有人谈“气”了,潘天寿坚持谈。等到今天,人人都在谈“气”,外国人也来谈“气”时,再读潘天寿的话,好像他谈得不足为奇。其实,不可忘记的是,他是在人人谈“形”的时候谈“气”的,他要以“气”挑战“形”,超越“形”。
潘天寿更为精彩的论述,在于对“线”的质量的见解。这出于他对绘画的深切体会,更显得分量沉重。他指出,要“凝炼中求畅快,畅快中求凝炼”。关于什么是好的“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英国古典画家荷加兹(W. Hogarth,1697—1764)认为,波浪线才是“有吸引力的线条”;一些现代艺术家,包括毕加索(P. R. Picasso,1881—1973)、勃拉克(G. Braque,1882—1963)、蒙德里安(P. C. Mondrian,1872—1944),特别是奥古斯特·恩德尔(A. Endell,1871—1925)则明确表示对几何图形和直线的爱好。中国人在谈论“线”的质量时,思路则与西方艺术家完全不同。他们所重视的,并不是“线”的几何特性,而是“作线”时的感受。“凝炼”与“畅快”两种感受相互交替,又相互包含,构成了“线”的节奏。这种“线”的节奏,不是从外在形体上见出,也不是像苏珊·朗格(S. Langer,1895—1982)所说的主体的“感受”(feeling)与客体的“形式”(form)之间的二元对立又“同形同构”的关系。那种“同形同构”的理论,是先把主客体分开,又在它们之间架起桥梁的做法。实际上,外在的“形”正是人的节奏性运动的结果,背后所蕴涵着的是人的气韵和神气。
这种“线”,尽管是人力而成,却又追求日积月累的自然力之效果。“古人言运笔作线,往往以‘如屋漏痕’‘如折钗股’‘如锥划沙’‘如虫蚀木’等语作解譬。盖一线之作成,原由积点连接而成者,故其形象直而不直、圆而藏锋,自然能处处停留含蓄而不信笔矣。”这正是潘天寿所追求的合造化之功,成画家之笔的意义所在。这种由气到意,到笔,再到墨所形成的“线”,体现了内在生命力。从潘天寿的一幅幅绘画作品中,我们才能体会到他所作的“线”之美。
在20世纪50年代初,笔墨被说成是“技法”。这种表述本身,就使它在当时的语境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当时的逻辑是:内容决定形式。“技法”是“形式”,于是,它就必须为“内容”服务,为“内容”所选择,随着“内容”的发展而被淘汰。实际上,内容与形式的两分,给艺术的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只有摒弃这个模式,运用当代艺术哲学的知识,才能对“笔墨”的意义获得正确的理解。
贡布里希(E. H. Gombrich,1909—2001)在论述中国绘画时,曾为一种现象感到困惑。他写道:“没有什么艺术传统像古代中国那样更强调需要灵感的自发性力量,但恰恰是在那儿我们看到一种完全对所获得的语汇的依赖。”他的困惑,恰恰说明了中国艺术的特点。在中国画中,“笔墨”是艺术的语汇,中国画家通过书法的练习,通过对传统名作的临摹,获得并掌握了这种语汇,通过对这种语汇的创造性运用,达到了心手一体的地步。这样的语汇影响着他们的视觉,使他们既通过“眼”,也能过“手”来看世界,从形形色色的世间万物中,看到其表现性。
他们也运用这样的语汇来捕捉他们自身的艺术感觉,将生活中的一些否则就会转瞬即逝的感受抽取出来,使之得到物质性的呈现。杜威(J. Dewey,1859—1952)曾写道:“画是抽出(draw out);是提取出题材必须对处于综合经验中的画家说的东西。此外,由于绘画是由相关的部分组成的整体,每一次对具体人物的刻画都被引入(be drawn into)一种与色彩、光、空间层次,以及次要部分安排等其他造型手段相互加强的关系之中。”画家将当下面对各种对象时的种种感受抽取出来,又将它投放当下正在受种种情境制约的关系之中并形成自己的活动。对于中国画家来说,使用笔墨的能力是他“抽出”当下感受所凭借的工具,通过具体的落笔用墨,他将当下的感受“引入”到绘画情境之中。中国画家讲“笔笔相生”,“下一笔看上一笔意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人们常说:我说语言,语言也说我。当人们运用一种不能熟练掌握的语言思维时,思维就木讷,说的话也简单。当人们能够熟练掌握了一门语言时,就能口若悬河,思如泉涌。绘画也是这样,“笔墨”是画家的语言,画家用它来寻找和抽取绘画的意义,同时也使这种意义获得表现。有什么样的画家,就有什么样的表现。同时,画家也是被造就的,他用“笔墨”,也为“笔墨”为用。画家处在“笔墨”传统之中,但画家要有所作为,将自己真实感受通过“笔墨”之“用”而表达出来。
三
潘天寿在关于绘画的论述中,很强调“布置”,或古人所说的“经营位置”。这可能与他身为艺术教育家有关。布置是一个具体的问题,但又与中国绘画的根本特性密不可分,在此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说说。
在绘画中,这儿画什么,那儿画什么,也许可以比作往一个房间里放家具。根据现有的空间,把家具放在恰当的位置。有艺术品位的人,就放得好看;没有艺术品位的人,就放得非乱即俗。这也许能成为经营位置的一种理解。
潘天寿写道:“西洋画的透视是错觉的科学,中国画的透视是幻觉的科学。实际上方桌的四边是一样长的,近大远小是眼睛的错觉。中国画根据作者和观众的心理要求,不受焦点透视的局限,按想象合理组织画面,这也是一种科学——艺术的科学。”依照想象去合理组织画面,这的确可成为“经营位置”的一种解读。
潘天寿还从自己的实践中,悟出了一些与“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相似的构图原理。例如,他指出,“大的、重的东西,可放在靠支点近的地方,而小的、轻的东西,可放在离支点较远的地方。此理亦即平衡。这种平衡不是靠相等的重量得到的,而是靠不等的距离得到的。这在艺术表现上就有变化。”类似的话,他还说过多次。例如,他的以中国的老秤作比喻:“老秤有秤纽、秤钩、秤锤三部分。物大而重,秤锤离秤纽就远;物小而轻,秤锤离秤纽就近,它以秤锤与秤纽相距多少进行调节,由于三者的距离不同,才能求其平稳而得势。”这些表述,与美国著名“格式塔”派心理学美学家阿恩海姆(R. Arnheim,1904-2007)在《艺术与视知觉》中的关于视觉的杠杆原理的论述,有很多相似之处。阿恩海姆详细而系统地论述了视觉的重力关系,讲大小、色彩、距离对重力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画上保持重力平衡对称的道理。我不清楚潘天寿有没有读过“格式塔”学派心理学的著作,他很有可能是从艺术实践中悟出了这方面的道理。
然而,潘天寿并不只是诠释阿恩海姆的观点。基于对中国绘画的了解,潘天寿达到一个与“格式塔”学派完全不同的结论。他所认为的平衡和对称,并不仅限于一种视觉上的静态平衡,而是一种与绘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动态过程。他对这种对象的理解,也不仅局限于认知领域,而且将人的活动放了进去。
由于中国画家既是用“眼”,也是用“手”来“观看”世界、作画的。这个观念,凝聚成一个词,就是“开合”。潘天寿指出:
绘画上的开合和做文章的起结一样。一篇文章大致由“起、承、转、合”四个部分组成。“承、转”是文章的中间部分,“起、合”是文章的开始与结尾。一篇长文章有许多局部有起结和承转,也有整个起结。一张画画得好不好,重要的一点,就是起结两个问题处理得好不好。
这种表述,既得中国古代绘画思想的精髓,又使其在现代发扬光大。因为,画是一种空间艺术,通过“开合”,就见出了时间性。这种时间性,不是莱辛(G. E. Lessing,1729—1781)在《拉奥孔》中所说的,通过选取最有意蕴的一瞬间来暗示时间,不是通过组画形成叙事时间,而是通过作画的起承转合过程来展示作画时主体运动的时间。这像做文章,文章要有顺序感,要层层推进,有铺垫,有高潮,再进入收尾。这也像作曲,从序曲,到展开,高亢与婉转相递,进入高潮,最后余音袅袅,进入尾声。这种“开合”,还要有相应和相破的关系,有过程的自然发展,有过程的突然转折,有顺势而下和逆势而上,有“山重水复疑无路”,并以此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种“开合”所带来的动态的过程,仍需要符合平衡的要求。然而,这种平衡,并非阿恩海姆式的只是视觉重量的平衡和对称。这种视觉重量的平衡和对称,当然是绘画所必需的。没有平衡和对称,绘画就会给人以不安的感觉。但是,潘天寿所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灵活的平衡”。他提出,“灵活的平衡,须先求其不平衡,而后再求其平衡”。这种“灵活的平衡”,只有将绘画作为一个过程,才有可能。作画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打破平衡,又实现新的平衡的过程。这种过程,有时会给人以一种意外的惊喜,从而达到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
潘天寿进而提出,从不平衡到平衡,甚至可由题款来实现。当画面留下不平衡时,最后,“以题款补其不平衡”。这种只有中国绘画才独具的平衡,当然是阿恩海姆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开合”源于气势。潘天寿指出,“故中国绘画在画面的构图安排上、形象动态上、线条的组织运用上、用墨用色的配置变化上等等方面,均极注意气的承接连贯、势的动向转折,气要盛、势要旺,力求在画面上造成蓬勃灵魂的生机和节奏韵味,以达到中国绘画特有的生动性。”这段话给予“经营位置”一个很精彩的解读。潘天寿还联系“气脉”“龙脉”等概念来深化这种对“经营位置”的解读,从而进一步升华对中国画的理解。
四
潘天寿的画,上承千年中国绘画的传统,下开新时代中国绘画之路。他所代表的美学理想,是共性的,中国绘画理想的精要在他身上有着集中而全面的体现;但另一方面,他又有着自己的独特、不可重复的特征。走进画展的展室,打开画册的册页,不用看署名,潘画的气势、气度和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潘天寿说,画中要有“我”。这个“我”,不可强求之,是日积月累的人生阅历和艺术造诣的体现,是修养在作品中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流露。但同时,这又体现了他长期的艺术追求。
用潘天寿自己的语言说,他的画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简”。“画事难于用繁,尤难于用简。简之可贵,在于纯炼。须老辣缜密,迹简意远,方为上品。”通过简,留下广泛的想象空间,也在传统风格的艺术中见出现代意味。
第二是“力”。他说画要强其骨,要“一味霸悍”。画要有力量,这个力量,是力能扛鼎,但又不是力士之力。我们听钢琴家弹出《黄河》的汹涌澎湃之声气吞山河,琵琶手弹出《十面埋伏》的金戈铁马之声,都具有无比的力量。画家也是这样,这是气之力、情之力,也是艺之力。
第三是“奇”。他强调在作画中要走极端。通过一种极端的状态,看视觉的可能性。人们常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当一幅画大开大合,被推向难处理的局面时,能使它峰回路转,复归平衡,就更能显示出画家的掌控力。这就像一位剧作家要有能力将戏剧冲突推向高潮,最后又复归平静一样。
这三个特点,是潘天寿在艺术风格方面的三个追求。在这些追求背后,他更加关注的,当然还是人格修养。潘天寿认为,中国画讲求修养。画要有“清峻之气,古朴之风,天真之美,自然之神”。这种修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至善人格,而是人生境界。达到这种境界,要有“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要历经人生磨难和艺术锤炼。王国维讲“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种境界不仅是学问之道,对诗人、画家也适用。
五
1970年,正值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潘天寿带着对中华文化的沉重忧虑,愤激地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难道对今后的中国就毫无用处了吗?传统越悠久,罪孽越深重,倒不如没有祖宗的好。”面对铺天盖地的“文革”洪流,人们不难体会潘天寿当时的心情。说完这段话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他是带着一种绝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难道中国画真的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没有前途了吗?不!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非写实的、讲究趣味和修养的中国画,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欧洲写实的绘画风格,到20世纪出现了重重危机。借助于数学、几何学、光学和色彩学的知识制造逼真的错觉,曾经是欧洲绘画的追求。当这种绘画理想被一些新的视觉图像的制作工具所取代时,艺术是否还在进步的问题,被严肃地提了出来。美国艺术家阿瑟·丹托(A. C. Danto)是这样谈论艺术的未来的。他说,艺术终结了,“艺术会有未来,只是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我们的艺术是已经衰老的生命形式”。他说的“我们的艺术”,是指欧洲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中叶的艺术。在这种艺术危机之时,迎来的却是多元文化的时代,是艺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代。
在新的时代,传统的中国艺术能否提供一种选择?中国艺术的笔墨趣味、动态构图,以及气韵格调,能否给饥渴的新艺术的探求者以滋养?这是当代艺术家们普遍探求的。美学家王朝闻(1909—2004)曾用“常”与“变”这一对范畴,来概括潘天寿的艺术。潘天寿的作品中,有“常”有“变”,但从总体上说,是“常中有变”。今天,我们看到了许多以“变”为主的艺术,人们用各种方式,挑战旧有的绘画观念。艺术需要多样化,要有各种各样的探索,不断地自我否定,也许正是当代艺术的生命力所在。但是,“变”中还是要有“常”。扎根中国古老传统的土壤,从现代社会汲取营养,面向丰富多样的艺术未来,这正是潘天寿给中国艺术之路的启示。在一个到处都在讲“终结”的时代,中国画需要再一次化茧成蝶,飞进当代世界艺术的百花园中。
编者注:该文刊发于《南国学术》2014年第2期第96—103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烦请继续向下拉,就可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