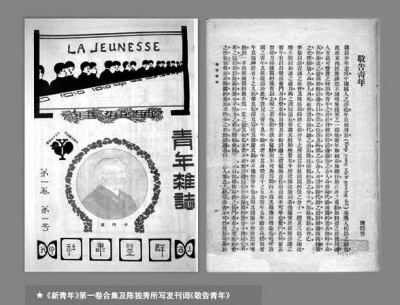陈世华 耿硕
【内容摘要】在20世纪初,日本的阶级艺术论争,是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和纯文学阵营之间展开的文学论争。20世纪10年代后期,以本间久雄、大杉荣和加藤一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阵营,明确指出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当下最重要的艺术,由此诞生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但这时的认识局限于对“民众”和“民众艺术”概念的讨论上。进入20年代后,以中野秀人和平林初之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认为,无产阶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无产阶级文化也是高于资产阶级文化的。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性质对比来看,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精神和文学精神都比资产阶级高贵,因此无产阶级文学也是优于资产阶级文学的,这就肯定了艺术的阶级性。而以菊池宽、久米正雄和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纯文学主义者,则主张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自律,即超阶级性,认为若无产阶级艺术从属于无产阶级运动,那么无产阶级艺术也就不可能存在艺术至上主义思想。阶级艺术论争是之后所展开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有力前提,也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的理论源泉之一。
【关键词】 阶级性;超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纯文学
一、日本的阶级艺术论争背景:民众艺术论争的升华
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三百多年闭关锁国的历史,西方产业技术、思想文化等迅速涌入日本,日本的社会体制也一夜之间从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并在短时间内向帝国主义方向发展。产业革命的突飞猛进和帝国主义财富的原始积累,促使日本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生存和独立自由而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斗争。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产生了指引产业工人争取自由、维护自身利益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1916年至1921年期间,日本诞生了以本间久雄、大杉荣和加藤一夫为代表的“民众艺术”理论,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产业工人对艺术的诉求,以及民众艺术对产业工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指导作用。但由于他们思想的局限,对“民众艺术论”的讨论停主要留在对“民众”和“民众艺术”概念的争论上,因没有具体的目标而显得有些空洞。但“民众艺术”论的讨论,却代表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它开始冲破长期被贵族和资产阶级文学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对创作和产生无产阶级艺术论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随着日本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这种纠结于概念上的争论,在实际生活中脱离了工人阶级,缺乏明显的无产阶级意识,显示出其脱离社会实际的一面。因此,以大杉荣为代表的民众艺术论者并没有真正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质,也没有明确提出改造社会的任务。将民众艺术论者的若干理论进一步发挥,并“最先论述文学的阶级性”的是中野秀人于1920年发表在《文章世界》9月号上的《第四阶级的文学》。同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的平林初之辅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将文学与艺术的阶级性向前推进了一步。宫岛资夫和有岛武郎等也都主张艺术的阶级性。
相对于中野秀人和平林初之辅等主张的阶级艺术论,菊池宽在大正11年(1922)《新潮》5月号上发表的《艺术本体无阶级》,主张艺术的本体是不变的,阶级艺术不过是“肤浅的问题”(菊池宽,1979:266)。久米正雄、芥川龙之介等主张纯文学的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艺术的阶级性也持否定态度。阶级艺术论争,就是在主张艺术阶级性的中野秀人、平林初之辅、宫岛资夫、有岛武郎等,和主张艺术超阶级性的菊池宽、久米正雄、芥川龙之介等之间展开的文学论争。阶级艺术论争不但是主张艺术的阶级性和超阶级性的两个阵营的讨论,也是日本关东大地震后所展开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有力前提。
二、无产阶级文学阵营:艺术具有阶级性
在《第四阶级的文学》中,中野秀人提出,虽然以前产生文学的最好土壤是贵族社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勇敢的人们开始来到了第三阶级的土地上”,而“到现在为止沉滞一律的文学,开始出现在了明快自在的世界”。也就是说,劳动阶级的文学开始侵入原先被贵族社会所垄断的土地,并且表现出了相当的活力。因此,中野认为现在的时代“变成了第四阶级的文学。但开拓新土地需要忍耐和勇气。”虽然在第三阶级文学的土地上种植属于第四阶级的文学需要忍耐和勇气,但“第四阶级的文学并不限于是由劳动者自身创造的,文学在穿着劳动服这一点上更看出其意义”。中野秀人已经看到全社会对第四阶级文学的支持,也对第四阶级文学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因为“文学是全人类的精神食粮。而且文学本身就是正义和自由的伙伴。解放是文学的本质。”中野秀人在论说了自己对当前社会的看法后,按文艺复兴、法兰西革命和俄罗斯革命的历史脉络论述了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就是感情本身。文学不能和某某主义同居。文学总是与正义和自由同行,但又不被正义和自由所禁锢”。这种将日本现状和欧洲文艺复兴、法兰西革命以及俄罗斯革命相比较的论述方式,极大地提振了自己用文学改造社会的信心和决心。中野秀人认为在日本当时的状况下,要想彻底获得正义和自由,就必须重视第四阶级的存在,重视第四阶级文学的重要性,“当下,除去第四阶级,文学就没有出路”。因为“对社会组织的探究才是第四阶级文学的特质”,“真正能了解社会组织的大概是艺术吧,我们必须破坏小艺术,创造大艺术”。这样,中野秀人就明确地把民众的观念发展到了阶级的观念,指出第四阶级是工人阶级,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当下最重要的艺术。中野秀人同时指出:
第四阶级的文学不是同情和怜悯的文学,而是反抗斗争的文学,是一点都不示弱的文学,是必须打破所有不愉快的文学。在此,即使说是第四阶级,仅仅表现在外在的还远远不够。伟大的作家始终处在第四阶级,觉醒的人始终是精神上的无产阶级。
中野秀人明确提出了文学“与正义和自由同行”,而争取正义和自由是第四阶级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通过文学探究社会组织,必须通过文学触及社会制度的真髓,从而指导第四阶级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抗和斗争。
继中野秀人之后,平林初之辅先后于大正10年(1921)在《新潮》12月号上发表了《唯物史观与文学》、大正11年(1922)在《播种人》6月号上发表了《文艺运动与工人运动》。《唯物史观与文学》首先批判了部分知识分子失去攻击目标的现实:“接受近世文化的教养,陶醉于精神主义福音的人看不见攻击的对象”,而“在看不见对象而闲得无聊的文明支配者面前,以大胆不敌的姿态出现的就是唯物史观”。平林初之辅批判了那种歌颂机械文明带来表象繁华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本质,没有革命的对象甚至是斗志。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引着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前进。文章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内容和《哲学的贫困》中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三个社会自身所具有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指出了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我们的解释是,唯物史观是根据物质的变化产生的。唯物史观是仅仅对该变化或者历史做出的说明,而不是要说明其发生和起源。
平林初之辅同时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几乎没有对唯物史观进行过研究,《唯物史观与文学》只是对唯物史观和文学,或者说和精神文化的关系发表的感想。因此,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平林初之辅暂时不可能对唯物史观的发生和起源有太深的研究和太多的论述。基于这种感想,平林初之辅对于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即使有人类的历史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这个事实,精神文化也依然是我们必须最尊敬的。相信唯物史观的人不但不忽视精神文化,反而是尊重精神文化。因此,我们要取代根据资本主义建立的文化,实现更加高等的文化,为此我们要改变物质条件。
平林初之辅明确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社会阶级对立上论述了物质条件和文学以及精神的关系,并指出无产阶级应该创造比资产阶级文化高等的文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改变第四阶级的物质条件。虽然平林初之辅并没有论述清楚无产阶级文学和工人运动的关系,但已经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是高于资产阶级文化的文化,同时也认识到了创造这种文化的物质要求。
为了进一步阐述文艺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关系,平林初之辅在时隔半年后发表了《文艺运动与工人运动》。在该文中,平林初之辅在指出明治以来文艺运动的特点是“流派和流派之间的运功”,“论争点主要是描写方式、本体,顶多是停留在对艺术价值的看法、人生观的不同”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特点:
最近开始兴起的阶级艺术运动,在其本质上,至少必须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现象、阶级斗争的局部战争、阶级战线的一部分的争斗,因此,不能理解为单纯的文学运动、纸上运动,而是阶级战主力军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胜。
平林初之辅的观点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其他流派的文艺运动区别开来,但同时也割裂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特性,也就是说,平林初之辅的这种观点有不尊重作为文艺的无产阶级文艺自律性之嫌。对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平林初之辅进一步规定了其性质:
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不是说流行作家坏话的运动,也不是举荐和拥护新进无名作家的运动。不是追究无名和有名、流行和非流行,而是阶级战。
其次,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与其说是文艺运动,倒不如说必须认识到首先是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其纲领不是文艺上的纲领,而必须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纲领。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唯一纲领。
平林初之辅这种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性质的规定,就完全使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从属物,也就完全否定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独自的地位和其自律性。基于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认识,平林初之辅认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对无产阶级大众运动起到协调联络作用。这一方面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要贴近大众生活,一方面也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特性,违背了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
宫岛资夫也先后在大正10年(1921)《解放》11月号上发表了《劳动文学的主张》,在大正11年(1922)1月的《读卖新闻》上发表了《第四阶级的文学》。在《劳动文学的主张》中,宫岛资夫首先主张文学的“技巧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东西”,但“以前称为技巧派的人笑话内容派的内容”,也就是说,技巧派的作家通过笑话内容派作家内容的幼稚而提高自己的主张。从整篇文章看,这里所批判的技巧派,是以菊池宽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学主张者,而内容派,也就是主张无产阶级文学或劳动文学的作家。宫岛资夫认为,这种过于主张技巧的技巧派作家,没有看到将来文学发展的方向,没有看到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学或者是劳动文学。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虽然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算强大,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支配权还占绝对优势,但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的丑陋,并已开始建设属于自己的新社会:
现在存在的被资产阶级认为是美的地方,对被掠夺阶级而言,一切都是丑陋的,被资产阶级认为是善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一切也都是恶的。被掠夺阶级所追求的,是打破这些所有的丑陋,破除这些所有的恶,努力建设新的美和新的善。
这就如宫岛资夫在文章开头表明的信念一样:“我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前,首先必须作为人生活下去”。也就是说要取代资本主义建立的文化,实现更加高等的无产阶级文化,我们就要改变物质条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时的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了建设新社会,建设属于自己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因为所谓资产阶级的善,“其道德的根基总而言之是意欲将他人隶属于自己”。这样,在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世界里,“没有个性的尊重,没有博爱的精神”。“在这样的境况下诞生的资产阶级艺术,何美之有,又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地方”。反观无产阶级,宫岛资夫认为:
其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显得丑恶、无知、迟钝和卑劣。但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不是只有希冀自己的幸福,他们不想将自己摆脱的痛苦再施加给他人,他们追求的是为了万人的幸福。……今天的无产阶级因为被长期榨取和压迫,饥寒交迫,而且其眼中燃烧着怨恨和憎恶之念。即便如此,他们也总是抱着追求全人类幸福的目标。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相比,无产阶级在追求独立自主的同时,还燃烧着博爱之心。哪个是美的哪个是高贵的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这种具有无产阶级精神的今天的劳动文学,可能还尚显幼稚,但其所具有的精神与资产阶级文学相比却可以说是高贵的多。而且,不管是被大众所欢迎,还是在文坛上被冷落,这种事怎么都可。我们只要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的艺术而彻底继续奋斗下去就好。
宫岛资夫通过对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认为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精神比资产阶级高尚,无产阶级文学的精神也比资产阶级文学的精神高贵,因此无产阶级文学也是优于资产阶级文学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追求的是人性,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观。基于此,宫岛资夫提出了对于无产阶级艺术家的要求:
就像在成为真的艺术家之前,必须作为人真实地生活下去一样,在成为真的劳动作家之前,必须作为真的无产阶级生活下去。
这就具体提出了对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的要求是必须首先成为无产阶级。这种要求,同样有要求无产阶级文学作家贴近大众生活的一面,但同时也否认了其他流派或者阶级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参与,是一种在无产阶级运动和文学高涨时期一种一叶遮目的思想。
《第四阶级的文学》中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中应享有和资产阶级平等的权利,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后,其行动才有了目标:
他们开始向社会要求将我们的生命归还我们,将我们生产的东西归还我们。这是近代劳动运动的根本精神……在第四阶级的这些要求中,没有像资本主义道德那样要求他人隶属于自己,没有被卑鄙的征服欲御使的权利倾向,也没有只是企图自己愉悦的利己主义。而是极小的、极正确的要求。
宫岛资夫认识到无产阶级开始对自己生命和物质生活有了明确的要求,并通过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比较,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道德的正义性。而要实现这种正义,就有必要由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引导第四阶级前进,“这是劳动者自身的劳动”。也就是第四阶级中的先觉者,一方面要代表第四阶级向社会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一方面要促进第四阶级的自觉。这种自觉要靠无产阶级文学来引导。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最终关系,宫岛资夫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目标:
我们在我们的阶级中,创造我们的美,否定恶,然后加紧迎接我们的生活和艺术达到完全一致的时代的到来。
从整个论述来看,宫岛资夫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也应该以去除对立阶级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为目标的,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将阶级意识进一步明确并为此而斗争。宫岛资夫对第四阶级文学的论述是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因此其论调难免有主观性的一面。但其论调中充满了阶级论,这种阶级论调,自然会表现在劳动阶级的文学运动上。
“白桦派”的人道主义作家有岛武郎,在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后,将拥有私有财产看成是人类之恶,而其说生活的时代恰好是日本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时期,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疯狂压榨产业工人,实现资本积累的时期。在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有岛武郎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向社会主义思想倾斜,并于大正11年(1922)在《改造》1月号上发表了著名的“一个宣言”,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艺术阶级性:
作为思想和现实生活相融合而产生的现象——总是将人间生活的统一,表现在最纯粹的形态上——最近在日本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一种运动,从所谓的学者或思想家手中,转移到劳动者的手中。而我所谓的劳动者,是指那些在社会问题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劳动对象,即第四阶级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
由此看出,有岛武郎认识到了当时日本的社会运动倾向,承认艺术存在阶级性,并预言社会运动将从学者和思想家之后转到劳动者本身手中,但有岛武郎同时强调:
我是在第四阶级以外的阶级里出生、生长和接受教育的,因此我是和第四阶级无缘的一个人。我绝对不能成为新兴阶级的成员,也并不想让我做第四阶级。我也不会作为第四阶级辩解、立论、运动之类那样愚蠢至极的虚伪之事。
有岛武郎虽然认识到了艺术存在阶级性,但认为由于教育和信仰的不同,属于第三阶级的自己不能指导第四阶级的艺术。有岛武郎的这种认识,“一方面说明有岛武郎认识到了社会问题的所在;一方面又对解决社会问题显得无奈,甚至是无能。”
无论是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中野秀人、平林初之辅、宫岛资夫,还是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有岛武郎,都认识到了日本近代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过程中,产业工人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对立,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迫切需要理论指导和文化指引,他们从道德、阶级、唯物史观等方面提出了艺术具有阶级性,并试图探讨第四阶级文艺工作者领导第四阶级革命的方法和可能性。
三、纯文学阵营:文学具有超阶级性
提出阶级艺术论的首先是无产阶级阵营,他们的主张虽然是侧重强调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对立,以及在这种对立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但对于无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学关系的论述,却明显带有无产阶级文学从属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倾向,这就否定了无产阶级艺术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特点,也自然会引起主张艺术超阶级性的文艺评论家的不满和批判。纯文学主义者菊池宽、久米正雄和芥川龙之介等,都反对艺术具有阶级性的说法。
菊池宽在大正11年(1922)《新潮》5月号发表的《艺术本体无阶级》,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认为艺术这种东西,和阶级没有关系”。并认为文艺只是艺术的一部分,而艺术是和阶级没有关系的。菊池宽进而论述道:
不是艺术的部分,比如其中被描写的题材、被描写的人物等这些方面,资产阶级强盛的时候会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如果无产阶级取得天下,也必然会带有无产阶级的色彩。……被描写的题材、思想和感情不是艺术的本体。如何观察、感受和描写这些东西是艺术的本体,那是艺术的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艺术的部分是和阶级无关的,是一成不变的。……。
因此,即使无产阶级的艺术崛起了,仅仅是其题材不同而已,其艺术作为艺术的原因一点都没有变化。
即菊池宽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时,无产阶级艺术可能带有无产阶级的色彩,这仅是其中的题材和人物等而言的,而艺术之所以作为艺术,其本体是一成不变的,是和阶级没有关系的。在艺术本来的部分中,显示出来的是超阶级的普遍性,也就是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自律。最后,菊池宽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主张:
如果无产阶级艺术存在的话,我想那也不是本体的问题,而不过是外皮或者说是形状的问题。因此,艺术的阶级性这种东西,我想是肤浅的问题。而且,我们说无产阶级的艺术,我想现在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到要求艺术的程度。现在的无产阶级首先要求的是像人一样的生活。我想无产阶级取得了像人一样的生活后,无产阶级的艺术才会成为问题。
菊池宽认为艺术的本体是不变的,即使有阶级艺术那也不过是“肤浅的问题”。而且,对现阶段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像人一样的生活”要比争取无产阶级艺术更为重要。菊池宽把争取“像人一样的生活”放在第一,其次才是争取无产阶级艺术。但他忽视了无产阶级艺术在争取“像人一样生活”和争取自由解放方面的作用,因此,不能把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割裂开来。
久米正雄在大正12年(1923)1月出版的《微苦笑艺术中》,发表了简短的评论《叩舷》。久米正雄首先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学者的特点:
无产阶级文学者各位的热情,或者是对公敌资产阶级,可能以彻头彻尾的憎恶反对为信条。但我们中间阶级者的悲哀无疑是,被旧体诗式的正义观念所囚禁,虽称为敌人,却要承认他们‘虽然是敌人,却值得敬佩的’事业。
久米正雄一方面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相两立,一方面也定性自己为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主张虽然存在社会阶级,但艺术中却没有阶级,当然也就不存在“阶级文学”。也就是,久米正雄是完全脱离阶级观点来看待艺术特点的,久米正雄的这种观点,“不是否定无产阶级艺术,而是从艺术的普遍性立场否定了阶级性”。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艺术是研究社会和人的重要手段。
芥川龙之介在大正12年(1923)《新潮》2月号上发表了《无产阶级文艺之可否》。芥川龙之介首先指出:“文艺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与政治无缘。毋宁说,文艺的特色也存在于同政治的关系之中”。同时,芥川龙之介认为:“当然,艺术至上主义者可能会说:因政治的原因,迟将文明传于后世是一种耻辱。我对这种艺术至上主义者抱有尊敬和好感。”芥川所希望的是“在于不问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要失去精神的自由。”因此,如果无产阶级的艺术至上主义者认为“除了无产阶级的文艺之外便再也没有可以促使人类进步的文艺”的话,芥川表示了否定和反对,因为其“对一切至上主义者——如按摩至上主义者也抱有尊敬和好感。”作为主张艺术至上主义者,芥川龙之介对无产阶级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存在嘲讽心理的,因为根据无产阶级艺术的要求,无产阶级艺术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运动,因此无产阶级艺术也就不可能存在艺术至上主义思想。
四、日本的阶级艺术论争的影响与现实意义
艺术是否有阶级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学自我确立的一般论,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起到了组织作用。就当时的现实看,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主张艺术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成熟于当时社会状况的先觉者,即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者指导。这种艺术理论虽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但阶级艺术论者充分认识到了民众对改变社会的诉求,以及无产阶级文学对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艺术论争,在理论上比之前的民众艺术论争前进了一步,促成了无产阶级文学成立的最初自觉。
艺术超阶级性论者并没有完全否定无产阶级文学,而是通过文学阶级性的有无间接地承认了无产阶级文学。从长远来看,艺术的阶级性仅仅是为了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真正的文学应该是超阶级的,它不属于任何阶级,它应该属于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最先进最朴实最勇敢最自由的人们。但纯文学阵营过分强调艺术自律,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忽视了当时日本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并迫切需要艺术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社会现实。因此,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和纯文学阵营之间的阶级艺术论争,实际上是两个阵营对对艺术追求功利性,还是追求自律的讨论。
早在1924年,毅夫就在《艺术评论》杂志上以《阶级艺术的主张》为题,翻译发表了同样主张阶级艺术论的文学评论家加藤一夫的评论,这是加藤一夫在1922年日本《改造》杂志3月号小特集“文艺与阶级意识”中发表的《无产阶级艺术要求其自身的文学》一文的节选。加藤一夫认为,“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唯物史观,使我们明白,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意识都是受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所支配。”由此可以看出,加藤一夫所指的唯物史观论者,显然就是指主张阶级艺术的平林初之辅。可以说,加藤一夫对日本阶级艺术论的介绍,对我国接受2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受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巨大影响,但从影响路向来看,却是两条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瞿秋白及‘太阳社’的蒋光慈、沈起予、钱杏邨等人直接传来;另一个是通过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以及鲁迅、冯雪峰、林伯修、陈勺水,胡秋原等人经日本文学界转折而来的。”但即使是同样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因传播者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也产生了一些论争。曾经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于一九二六年发表《文艺家的觉醒》《革命与文学》等文,鼓吹‘站在第四阶级(立场上)说话的文艺’,要求作者‘表同情于无产阶级’”,同样曾经留学于日本的鲁迅,也引用了第四阶级理论,充分肯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到后来,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普洛文学”的倡导者,和鲁迅发生了激烈的理论论争。论争原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十分复杂,但创造社和太阳社是受瞿秋白盲动路线的影响,否认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界限,贬低了“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新文学。而鲁迅恰恰抵制和反对了瞿秋白的错误路线,阐明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文艺运动性质的认识。也正因为对问题的认识差异,才产生了这次众所周知的大论争。
我国30年代的文学论争,除无产阶级文学论争外,还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大众化问题论争、文艺与人性的论争等等,这些论争是各种文学力量之间的对立、斗争和矛盾,“涉及的问题看起来非常多,但是不少都直接或间接地跟意识形态重建的目标和方向有关”,也就是说,文学论争的直接原因不是文学,而是文学背后的政治目的。朱晓进也认为30年代有关文学问题的种种论争,“起因往往是来自于非文学的因素,即论争的出发点首先不是出自文学自身的考虑”,而“从政治化角度看问题,是30年代文学论争最基本的也是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看来,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还是侧重于和政治的联系,也就是文学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占据上风,但这也是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重要文学现象。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卷第2期。作者陈世华,文学博士,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及文论研究;耿硕,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本文为2013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近代文学争论研究”(项目编号:13WWB008)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