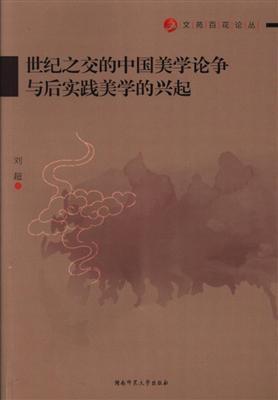王晓华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 要]作为实在的活动,实践的承担者只能是身体-主体。离开身体-主体来谈论实践,就无法敞开其实在品格,以实践为原初范畴的美学建构便会处于悬空状态。从这个角度看,实践美学的最大欠缺是对身体-主体的忽略。忽略身体而又强调实践的意义这种自我矛盾的做法不但造就了一系列逻辑悖论,而且使实践美学无法回答许多根本性的美学问题。后实践美学的倡导者虽然力图超越实践美学,但同样未意识到身体-主体的意义,因而也将实践美学的逻辑欠缺带到自身的理论建构中。只有敞开了实践、生存、生命对身体-主体的原始归属关系,我们才能超越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共同欠缺,建构出圆融的、具有独创性的、富有解释力的汉语美学体系。
[关键词]实践美学 后实践美学 身体主体 缺席 欠缺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2— ),男,吉林省吉林市人,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文化理论研究。
实践美学虽然对当代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其逻辑上的欠缺也使它成为批评和挑战的对象。从杨春时1994年发表《走向“后实践美学”》起,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已经持续近二十年了。意味深长的是,曾一度咄咄逼人的后实践美学并未将挑战的气势转化为论战的优势,其与实践美学的博弈至今仍处于僵持状态。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后实践美学非但没有克服实践美学的最重要欠缺,而且将这种欠缺带到自身的理论建构中。从逻辑上讲,实践美学的最大欠缺是对身体-主体的忽略。实践之区别于精神活动,在于其实在品格。作为实在的活动,它只能由实在者承担。这实在者就是身体。身体是实践的承担者,实践的主体是身体。离开身体-主体来谈论实践,就无法敞开其真正的实在性,以实践为原初范畴的美学建构便会处于悬空状态。吊诡的是,对身体-主体的忽略却是实践美学一以贯之的特征:无论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还是邓晓芒、易中天、张玉能等人倡导的新实践美学,都没有从身体-主体出发来阐释实践(劳动)。杨春时敏锐地发现了实践美学的这种悬空品格,指出不重视身体性的实践美学“仍属于意识美学”。 令人遗憾的是,他本人在建构后实践美学时并未因此明确承认身体是实践、生存、审美的主体,而是回到了二元论立场:“应该超越意识美学与身体美学的对立,既承认审美的精神主导性,也承认审美的身体性,从而成为身心一体的现代美学。”既然精神在审美过程中是主导性的,那么,身体就注定是从属性的存在,所谓“身心一体的现代美学”归根结底是精神美学。在不承认身体的主体性这点上,杨春时的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并无二致。
以实践为原初范畴而又回避身体的主体地位,这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理论立场。实践美学属于唯物主义理论家族,而唯物主义认为精神不过是物质的活动-功能,因此,从唯物主义出发的实践美学理应承认身体的主体地位。将意识归结为身体(物质存在)的功能却又以机械论的态度对待身体,是传统唯物主义的重要缺陷。由于这种缺陷的存在,提倡物质一元论的当代西方哲学家“更倾向于使用物理主义(physicalism)这个术语”,以之表示物质自身就可以运动和发展。马克思提倡实践概念的本来意图就是克服“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但他因为聚焦于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未展开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肉身的主体”概念。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研究表明精神不过是身体的功能,与独立精神实体(如灵魂)相关的观念群则常常被摒弃。④正是在这种语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梅洛-庞蒂写下了《知觉现象学》,正式以身体-主体(body-subject)概念取代精神-主体(mindsubject)范畴。对于梅洛-庞蒂的上述思路,美国学者丹尼尔·科拉克(Daniel Kolak)和英国哲学家西门·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标志着西方身心观的根本转折。遗憾的是,梅洛-庞蒂尽管在汉语学术界声名显赫,但其身体-主体思想却未获得中国主流学者的恰当评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也没有因为他的影响而在实践概念和身体-主体范畴之间建立正面的理论关联。这种原初性的欠缺既使实践美学在逻辑起点处和建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也使后实践美学无法真正超越实践美学。
一、身体-主体的缺席与实践美学的逻辑悖论
实践是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李泽厚曾明确表示自己“从实践出发研究人的认识”。邓晓芒、易中天、张玉能等新实践美学的倡导者也都将实践当作原初范畴。然而,实践并非自明性的概念,以实践为逻辑起点和原初范畴的美学建构首先应该回答:何谓实践?恰恰是在阐释实践概念的过程中,实践美学暴露了其在逻辑起点处就已生成的悖论。
从逻辑上讲,实践总是某个主体的实践。要回答“何谓实践”?就不能不回避“谁在实践”。吊诡的是,实践美学并未深入探讨主体问题。在李泽厚、邓晓芒、张玉能等人给出的实践定义中,主体不是被含混地等同于“人”或“人类”,就是被忽略了:(1)“人类以其使用、制造、支配工具的物质实践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李泽厚);(2)“实践又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情绪的物质生产活动”(邓晓芒);(3)“实践是一种多层次累积的结构”(张玉能)瑏瑠。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状态时,实践本身直接被当作活动的承担者:
人类社会实践在长期活动中,由于与多种多样的自然事物、规律、形式打交道,逐步地把它们抽取、概括、组织起来,成为能普遍适用、到处可用的性能、规律和形式,这时主体活动就具有了自由,成为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
按照这种表述,与事物打交道的主体就成了“人类社会实践”。可是,“人类社会实践”是一种活动,不是独立的主体,断言“人类社会实践”与什么打交道显然说不通。实践美学家之所以提出如此含混的命题,是因为他们的主体观出了问题:将主体认作“人”或“人类”,而人类的基本生存活动又是实践,因此,他们时常将人类与实践划上等号。然而,人、人类、实践皆是共名,以人类和人类实践为主体不但遮蔽了主体的个体性,而且无法在身心观层面明确回答“谁在实践”这个关键问题。这种遮蔽和回避对实践美学来说是个重要的欠缺。它最终将其理论建构置于不可解的逻辑困境中:在谈及审美的起点和原则时,以“人”、“人类”、“实践”等为原初范畴尚可自圆其说,但在进入审美的感性、个体性、心理性层面以后却不能不触及审美的精神性,身心问题再次凸显出来;由于未敞开实践与身体-主体的原初关系,实践美学家难以找到将物质实践与精神性审美统一起来的现实路径;它先是选择将社会存在和文化-心理本体并列的二元论立场,而后索性将心理本体当作审美的主体;于是,便有了实践美学蜕变为精神美学的逻辑悖论。
早在李泽厚阐释主体性哲学的基本内涵时,上述悖论就已经显现出来:“人类主体性既展现为物质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核心),这是主体性的客观方面即工艺-社会结构即社会存在方面,基础的方面。同时主体性也包括社会意识亦即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观方面。”在这里,社会实践被等同于“主体性的客观方面即工艺-社会结构即社会存在方面”。可是,既然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体,那么,社会意识就只能从属于它,为何又将工艺-社会结构(等同于社会实践)和文化-心理结构并列起来呢?显然,双重本体说的出现表明实践美学的逻辑体系出现了内部分裂。造成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实践美学找不到将实践/审美、社会/个体、理性/情感统一起来的东西,只好采取“恺撒的归恺撒,耶稣的归耶稣”的二元论建构策略。对此,实践美学阵营内部某些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已有领悟:
用传统实践范畴解决不了美的本质问题,主体性实践美学……于是搁置或抛弃实践观点,转向“心理本体”或“感性生命本体”,结果便形成了美的根源的客观社会性与美的本质的主观心理性的二元对峙。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未找到能将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统一起来的主体,觉察到了上述问题的实践美学家同样找不到消除二元对峙的方法。为了避免重蹈二元对峙的覆辙,后起的实践美学家普遍试图用三分法代替李泽厚的二分法。例如,张玉能将实践划分为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价值评估层,认为三者的关系是:“从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实践的物质交换层,既是实践的意识作用层和实践的价值评估层的基础,又受到两者的指导和制约。”可是,这种划分方法岂不是同样将实践的物质之维和精神之维分置两端,这与李泽厚的双重本体论又有何区别?再如,陶伯华将实践主体的活动划分为精神意向活动、工具技术活动、人际交往活动,但这种三分法依旧把精神活动与社会实践放在不同的层面,仍是将精神意向活动当成审美的承担者。事实上,只要不找到能将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统一起来的主体,就不能消解二元论,这在邓晓芒和易中天的表述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他们为了消除双重本体的悖论,强调“实践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本身所固有的精神要素”,断言意识具有三重超越性:
1.意识使动物也有的对客观外界的直观的“表象”,上升到了人的“概念”;2.意识使动物也有的对自己生存必需的物质对象的“欲望”,上升到了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意志”;3.意识还使动物也有的由外界环境引起的盲目的“情绪”,上升到了人的有对象的“情感”。经过如此这般的话语转换,意识就又像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那样成为事实上的主体,实践美学的的确确蜕变为杨春时所说的意识美学。尽管邓晓芒强调意识的超越性“最终仅仅是实践的产物”,但这种强调更多地是一种立场表述而非具体的阐释,实践美学的问题依旧存在。
从本文作者的角度看,实践美学之所以在逻辑起点处就生发出不可解的悖论,根本原因在于对身体-主体的忽略。实践是一种实在的活动,实在者才能实践,因此,实践的主体只能是实在的身体。离开了身体-主体,实践不过是个空洞的概念。只有敞开了实践对身体-主体的原初归属关系,相应的逻辑悖论才能被真正消解:(1)身体是生存实践的主体,审美活动不过是生存实践的内部构成(内部过程),超越性归根结底是身体-主体的超越性;(2)对于身体-主体来说,最根本的活动都发生于实在者与实在者关系的层面,凡是演绎这种关系的活动都从属之,因而实践中的心理-文化结构与工具-技术结构的对峙仅仅是美学家的虚构;(3)任何实在者在某个时刻都在宇宙中占据独一的位置,身体-主体与其他实在者的位置无法重合,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对象化,只能在顺应后者自立性的前提下建构属己的世界,而审美则诞生于这种建构实践。
二、离开了身体-主体的实践美学难以敞开审美的发生机制
除了在逻辑起点处的悖论外,实践美学对审美发生机制的解释也有牵强乃至矛盾之处,受到了后起美学家的广泛批评。从本文的立场上看,这种困境同样源于身体-主体在其体系中的缺席。
在探讨美感和审美能力的生成机制时,李泽厚曾提出著名的积淀说:
要研究理性的东西是怎样表现在感性中,社会的东西怎样表现在个体中,历史的东西怎样表现在心理中。后来,我造了“积淀”这个词,就是指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成了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
“积淀说”的提出固然使中国美学研究从侧重于客体的范式转向对主体的研究,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1)过于强调个体-主体的被动接受而忽略其主动建构,“没有进一步揭示个体审美心理的共时性结构”,“可能导致心构的遗传决定论和宿命论”;(2)积淀这种很可能不确切的比喻至多说出的是生存实践的结果,而非审美心理生成的具体机制。这两种欠缺都与身体-主体的缺席直接相关:其一,由于与具体的、感性的、此在的身体-主体失去了联系,李泽厚的实践概念无法指称个体的生存,难以敞开个体在审美心理生成过程中的主动性;其二,这种分离最终使实践概念只能表征无主体的活动,从无主体的实践出发自然不可能揭示主体审美心理的生成机制,只能以模糊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大体思路。新实践美学的建构者部分地意识到了李泽厚实践概念的空泛品格,但依旧未发现实践对身体-主体的原初隶属关系,其推理最终没有通向对前者的实质性超越。比如,邓晓芒一方面指责李泽厚“从实践中排除了人的主观因素”,一方面又含混地将实践界定为“主客观的统一”,实际上又恢复了前者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样式,并因此合乎其自我逻辑地宣称“审美活动是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 这种阐释至多部分地克服了旧实践美学对个体主体性的忽略,仍未言明审美主体的具体身份和审美生成的具体机制。“人化对象”说不仅停留在传统实践美学的语境中,而且同样失于笼统:“人化”即对象化是怎样发生的?身体在对象化过程中究竟是主体,还是仅仅是行使物质生产功能的中介?倘若身体是实践的主体,那么,身体性对人化对象活动有何具体的规定?对于这些问题,邓晓芒没有给出答案。再如,为了消解“人化对象”的单面思维,张玉能提出了“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的双向对象化概念,认为“正是这种实践的双向对象化决定了审美活动中美和美感的同生共在”。客观地讲,双向对象化说显现了审美生成机制的复杂性,确实优于先前的“人化对象”理论,但它没有回答两个关键问题:双向对象化如何可能?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其机制是什么?不深入到具体的主体层面,这个问题显然是无法回答的,而张玉能将物质与精神分立的做法又意味着他没有重构真实的主体,所以,他对审美发生机制的阐释最终未完成对实践美学的实质性超越。
越是落实到细节处,实践美学的欠缺就显现得愈加明晰。形式是实践美学的重要范畴。李泽厚曾将美定义为自由的形式:“自由的形式就是美的形式。就内容而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强调美与形式的联系是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路,实践美学重视二者的关系说明它深入到了美学建构的细节层面。不过,在审美与形式的关系已经受到普遍肯定的当代,再简单地肯定之并无太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揭示形式生成的具体机制。由于脱离了身体-主体谈论形式感的生成,实践美学的答案依旧显得空泛。在论述形式生成的具体路径时,李泽厚又提出了“社会劳动”中的“抽象说”:
……原始人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对自然的秩序、规律,如节奏、次序、韵律等掌握、熟悉、运用,使外界的合规律性和主观的合目的性达到统一,从而产生了最早的美的形成和审美感受。也就是说,通过劳动生产,人赋予了物质世界以形式,尽管这形式(秩序,规律)本是外界拥有的,但却是通过人主动把握、“抽离”作用于物质对象,才具有本体的意义的。虽然原始人群的集体不大,活动范围狭隘,但他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群体,正是在这种群体在使用、制造工具的领导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劳动”关系。只有在社会性的劳动中才能创造美的形式。
将美的形式与社会劳动联系起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对形式的有意识把握为人所独有,那么,它必然产生于人独有的活动,而能进行复杂的“社会劳动”恰恰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基本特征,因此,上述说法至少揭示了形式感和形式意识产生的部分机制。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美的形式如何产生于社会劳动中的?对此,李泽厚的回答是:抽离于物质对象(对自然规律的形式化抽离)。可是,抽离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为什么动物不能抽离?抽离缘何偏偏发生于社会劳动中?由于离开了身体-主体来谈论社会劳动,李泽厚只好不断重复其“积淀说”和“抽离说”,始终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新实践美学的几个代表人物———邓晓芒、易中天、张玉能等———虽然更加强调实践的建构功能和超越性,但均未回答上述关键问题。
事实上,不具体化到个体-主体层面,就无法真实地重构人的社会实践,自然难以解释形式感在社会实践中具体的诞生机制。实践美学之所以在解释审美机制时陷入困境,根本原因是离开了身体-主体来研究实践和劳动。倘若敞开实践对身体-主体的原初隶属关系,那么,我们就不但能化解上述困境,而且可以敞开“美的形式”与“社会劳动”的基本关系:(1)作为实在者,身体-主体在某个时刻只能占据一个位置,故为了形成一个活动体系,人必须与其他身体-主体合作,也就是说,实践原始地是社会性的;(2)联合中的人生产出变化的活动结构并以这结构同化对象(涵括)对象的结构;(3)在生产出各种活动结构的同时,人不断对其进行运演(包括抽象),这种运演使人获得了各种基本形式;(4)形式感产生于联合着的身体-主体对其活动结构的运演,“美的形式”便出现在此过程中。当然,以上演绎仅仅是众多可能的演绎之一,本文以它为例是想说明:只有回到身体-主体,实践美学才能具体地解释审美的诞生机制。
三、未回归身体-主体的后实践美学无法克服实践美学的欠缺
实践美学的欠缺源于对身体-主体的遗忘,因此,只有回到身体-主体,才可能超越其局限。可以通过分析后实践美学的两个重要派别———超越美学(生存美学)和生命美学———来证明这点。杨春时是最早提出后实践美学的学者之一,其倡导的超越美学亦成为后实践美学的重要流派。他反思实践美学对总体性社会实践的推崇,强调审美是超越共性、现实、劳动的“自由精神生产”。为了克服实践美学的欠缺,他认为美学建构应该从比实践概念更基本的范畴出发。经过推理,他将“人的存在即生存”设定为超越美学的逻辑起点:
人的社会存在即生存,万事万物都包括于生存之中,它是第一性存在,是哲学反思唯一能肯定的东西,因而也是美学的逻辑起点。生存以实践(物质生存活动)为基础,但又超出实践水平,更为全面、丰富。我们以生存论为美学的逻辑起点,推导出美学范畴体系和
审美的本质规定。
以人的生存为逻辑起点,这本身并无逻辑上的不通之处。问题的关键是:是谁在生存?生存的基本规定是什么?从杨春时的表述来看,超越美学的生存概念“以实践为基础”。既然以实践为基础,就应该承认实践者———身体-主体———的地位,然后才能现实地超越实践美学。令人遗憾的是,超越美学并未抵达这个结论,而是表示自己“既承认审美的精神主导性,也承认审美的身体性”。显然,在主导性的精神面前,身体只能是第二性的存在,属于精神升华和超越的对象,当然没有资格荣登主体之位。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逻辑前提,杨春时在列举了自然生存方式、现实生存方式、自由生存方式之后,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审美及其反思形式是不依附于物质生产的‘自由精神生产’。”在这个表述中,关键词无疑是“精神生产”。然而,经过如此这般的转换之后,超越美学岂不成了杨春时所反对的“意识美学”?它难道不是与他所批评的实践美学殊途同归了吗?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超越美学的生存概念同样脱离了身体-主体,因而只能指称人的精神生活;于是,在具体的理论推演中,“生存”马上被“精神”所取代,超越美学(生存美学)则显现为精神美学。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倘若超越美学不克服实践美学的根本欠缺———对身体-主体的遗忘,它就无法完成对实践美学的全面超越。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生命美学中。作为生命美学的倡导者,潘知常曾表示自己要“从实践活动原则转向人类生命活动原则”,让美学在“人类生命活动的地基上重新构筑自身”。与杨春时一样,他不仅强调自己的美学建构从生存(生命)出发,而且强调审美活动对实践的超越:“审美活动也不就是实践活动,而只是实践活动的超越(正是因为实践活动的不自由,才导致了审美活动的诞生……)。”甚至,生命美学的宣言与超越美学也极为接近:
生命美学以生命这一更具本源性的范畴为人的审美活动注入活力,以对实践这一物质活动的超越切近了审美作为一种促成的精神活动的实质,以审美的一元性超越了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和实践美学相比,这应该是一种更具本源性的美学,是一种靠对生命的体验和直观“直指本心”的美学,是一种首先抓住美的超越性这一本质性的规定然后重新向现实敞开的美学。
恰由于生命美学与超越美学的同构性,它也与前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生命属于谁?是实践着的身体-主体,还是超越性的精神?如果是后者,它如何解释自己与实践美学(最终诉诸心理本体)的区别,怎样敞开超越实践美学的具体机制?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潘知常所说的生命活动并未落实到身体-主体,其生命美学依然是“直指本心”的精神美学。与其说这种避开身体-主体的美学是后实践美学,毋宁说它把实践美学强调精神主体性的维度最大化了。事实上,在其后期建构中,实践美学的代表性人物李泽厚表达了同样的思路:
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性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吧!不要再受任何形上观念的控制、支配,主动来迎接、组合和打破这积淀吧。艺术是你的感性存在的心理对映物,它就存在于你的日常经验中,这即是心理—情感本体。
尽管上述思路同样表达了晚年李泽厚对其实践美学体系的反思,但它并未完成真正的自我超越,而是将身心二元中的一方———精神———发展为主导性的概念。于是,心理-情感成为日常经验的主体,身体被彻底放逐了。与后期李泽厚的思路一样,“直指本心”的生命美学也最终将精神性存在当作了本体,它所说的整体性和诗性都是精神本体的特征。从根本上说,这种以精神为主体的美学是“非”实践美学而不是“后实践美学”。
超越美学和生命美学是后实践美学的两个重要流派。它们折射出后实践美学的总体欠缺———绕过了身体-主体谈论对实践美学的超越,因而其思路并未真正超越前者的逻辑脉络。真正的后实践美学应该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实践美学,亦即将其合理性涵括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实践美学的主导范畴是实践,实践是人与世界实在的生存论关系,审美就从属于这种实在的生存论关系整体。如果绕过这种实在的生存论关系,那么,所建构出的就仅仅是“非实践美学”。要从人与世界的实在关系出发,就不能不找到建构此实在关系的主体。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身体。身体不是惰性的存在,不是精神的临时居所,不是审美发生的场地,而是具有自我设计、自我创造、自我领受功能的主体。实践、生存、生命活动都属于它。只有在敞开了实践、生存、生命对身体-主体的原始归属关系之后,人才能真正破解审美之谜。
离开了实在的身体-主体来谈论实践、生存、生命是实践美学和实践美学的共同欠缺。要克服这种不足,美学研究就不能不回归感性的、此在的、实践着的身体-主体。这并不是说回归身体-主体可以解决相应美学建构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而是强调此乃超越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欠缺的必经路径。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主体性理论视野中的身体美学建构:主体论身体美学研究”(07j01)的阶段性成果〕
1杨春时:《意识美学与身体美学的对立之消解》,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1)。
2Simon Blacknurn,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press, 1994, p.287、357.
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1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李泽厚:《美学四讲》,第45、48、78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6邓晓芒:《什么是新实践美学?》,载《学术月刊》,2002(10)。
7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陶伯华:《美学前沿———实践美学新视野》,第1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邱明卫:《建构———积淀与超越的中介》,载《学术月刊》,1994(4)。
10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载《学术月刊》,1994(5)。
11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第18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
12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第56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13潘知常:《超越主客与美学问题》,载《学术月刊》,2000(11)。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1年5月第43卷